阿瑞尔·道夫曼(Ariel Dorfman)的作品常常用细致入微的描写,揭露野蛮的独裁者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和折磨——譬如纳粹主义、特朗普主义,以及智利的皮诺切特独裁,甚至是唐老鸭。但是这位作家本人却面容和善,带着温暖亲切的好莱坞演员式的招牌微笑,除了索尔·贝娄以外,我再想不出有哪个“严肃”作家能像他这样和蔼可亲了。
同时身兼小说家、文学评论家、诗人、戏剧作家、教授、记者、影视编剧和社会活动家,道夫曼的经历复杂而多面。他的父亲出生于美国奥德萨市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母亲则有着比萨拉比亚犹太人的血统。道夫曼出生于阿根廷,两岁便随父亲躲避庇隆军队的抓捕而逃到美国。他的父亲虽是联合国高官,但因为当时的麦卡锡整治巫术,一家人又被迫迁徙,这次的目的地是智利。
道夫曼获得智利公民身份时已经二十多岁了,这时他又远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深造。毕业后的道夫曼回到智利,这时正值1970年代早期,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总统,道夫曼在他麾下任文化顾问一职。1973年皮诺切特的军事政变结束了一切,道夫曼被迫流亡。在这之后,他辗转于巴黎、荷兰,又再度回到美国。
道夫曼人生如戏,这些只是他一生经历中几段高潮的高度浓缩。1994年,罗曼·波兰斯基执导《不道德的审判》(Death and the Maiden),由西格妮·韦弗(Sigourney Weaver)和本·金斯利(Ben Kingsley)主演,这部电影就是根据道夫曼的同名戏剧剧本改编的,也让这位作家声名鹊起。今天,这位赫赫有名的作家常往返于美国与智利——因为那里的民主制度终于恢复了。

尽管道夫曼平易近人,性格活泼,他骨子里还是一个严肃的人。他坐在酒店咖啡厅的窗边,指着窗外西北方向的马萨诸塞大道说,“智利人对使馆街有一种特殊的情感,”道夫曼变得肃穆起来,他指的是1976年9月的汽车爆炸案。皮诺切特的秘密警察在智利使馆前的街道上放置了一颗汽车炸弹,导致当时的智利国防部部长遇害。从酒店窗户望出去,案发地点清晰可见。
和他以往的作品一样,道夫曼的新书《达尔文的幽灵》(Darwin's Ghosts)也探讨了权力斗争、身份认同与帝国。故事始于1981年9月11日,正好是9·11恐怖袭击的二十年前(也是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后的8年)。这一天,书的主人公菲茨罗伊·福斯特(Fitzroy Foster)14岁了,父亲给了他一台宝丽莱相机,庆祝他的生日。然而,在拍出的一张照片中,隐约可见一个暗影,像个幽灵。那其实是一个风尘仆仆的男人。福斯特发现,这个男人带领着他的人民经历了长途跋涉,他们都是一场暴行的受害者。男孩便和他的女友卡姆(Cam)一道,像奥德修斯一样开始了一场十年的旅程,去寻找这个男人,去了解他是谁,去弄明白自己能为这项罪行做些什么,去揭露那些罪恶——那个历史的幽灵。

道夫曼将自己视为“文化之间的桥梁”。福斯特是个典型的美国人,年轻幼稚、娇生惯养,而在他的冒险中,这个年轻人不得不面对道夫曼和他的国人当年经历过的遭遇。当然,这也永远地改变了福斯特。道夫曼形容《达尔文的幽灵》讲述的是“人们从一个环境到另一个环境转换过渡”的过程。他希望自己能像卡夫卡一样,营造一种唤起人们幽闭恐惧症的气氛,表现人们在尘世和灵界之间徘徊的焦虑彷徨。道夫曼在这点上干得漂亮。不过这本小说还不仅是卡夫卡式的反思,更是一部恐怖小说,一部神秘的鬼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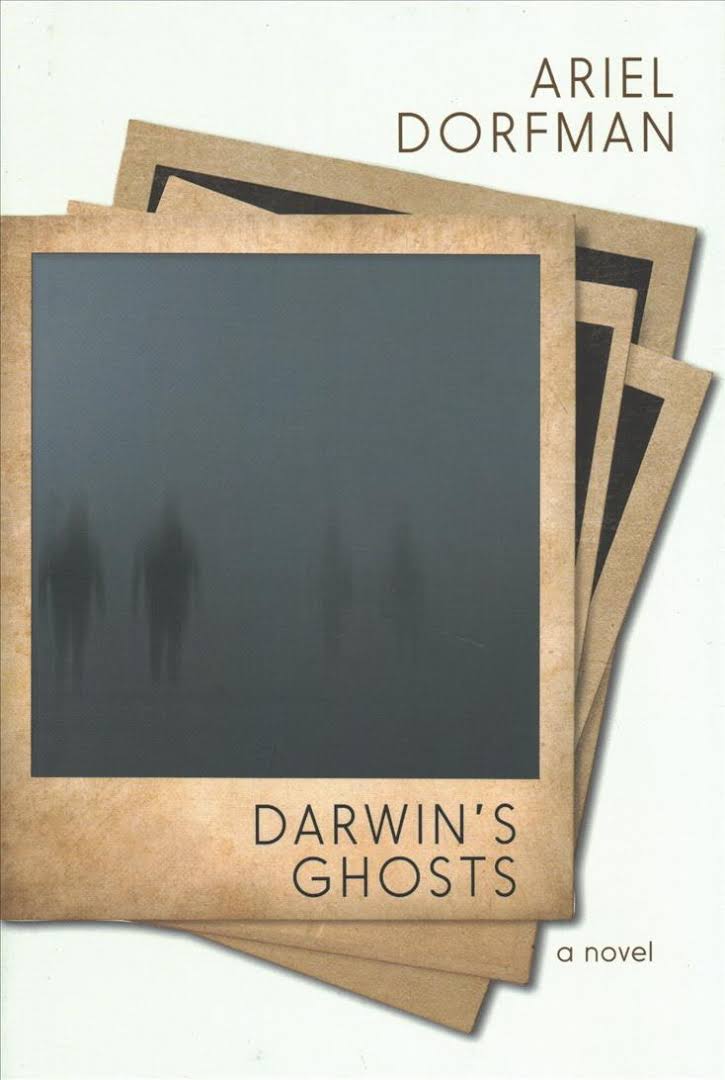
和菲茨罗伊·福斯特一样,道夫曼自己也是一个漫游者。和他聊天不谈到旅行、流亡和相异的他者简直是不可能的。在过去的一整个世纪里,道夫曼家庭都在动荡中奔走。先是欧洲的战争和反犹主义运动,逃亡到美洲新大陆也并没有让日子好过一点。“屋子里那些人我素昧平生,”道夫曼回忆道,“但单凭他们手中的一支笔或是一条情报”,就能让道夫曼与家人再次背井离乡。
能够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要住哪,对道夫曼来说是一种奢侈,“历史总是横插一脚。”十年流亡生活后,道夫曼回到智利。这时候的故乡已经恢复了民主制度,重建了正义和人权。然而道夫曼竟再度被捕,被驱除出境。他的妻子安赫利卡放心不下,让他暂居国外,等到智利的政治环境好转了再回国。
今天的道夫曼想去哪就能去哪,但这并没有让他对国家的认同和归属感来得更容易些。他频繁地回到智利,但常常说,“显然我不再属于智利了。”如果说智利是“家”,那么回家对他来说就是回到一个不存在的地方。不过,结婚后,这对他来说这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家就是我毕生至爱所在的地方,”道夫曼继续说,“家就是我52年的妻子所在的地方。”
道夫曼讲起这种感觉,他可以生活在任何一个地方,却没有一个地方能给他归属感——他总是一个异乡人,一个观察者。“对作家来说,没有归属感甚至流离失所都不是一件坏事,”他顿了顿,“只要你能好好处理它,不被这种感觉打败。”道夫曼说,要在这漂浮不定的生活中生存下来,你得有一个道德罗盘,以及一个稳固的家庭。“我更像是一个流亡者,而不是旅行家。换言之,我不会想着如果不能到达目的地我将面对什么,更加关注我脚下所走的路有没有偏离。”
所处的地区和身份认同和语言密不可分。在童年时代,道夫曼只会说西班牙语。一场厄运让他的生活发生了改变。来到纽约不久,他就染上了肺炎住进医院。当他从上帝的锡安山重回人世间,往后的十年里,都没有再说过一个西班牙语单词——十年这个荷马式的时间跨度也值得玩味。不久,道夫曼一家再次回到智利,他又得重新开始学习西语了。
道夫曼称自己为“语言的原教旨主义者”。移居智利后的许多年里,他都把自己看作一个以西语为母语的人,反而抗拒起英语来。然而,最终他还是靠着自己的英语写作能力养活了自己,也因此不得不接受自己确实是一个“彻底的双语使用者,而且拥有二元文化背景”。他无法否定哪一种语言,更无法两者都抛弃。
这种语言的循环复现和双重性也塑造了他的写作生涯。道夫曼同时还能说意大利语、法语等语言,不过主要用英语和西班牙语写作。《达尔文的幽灵》就是一部英语作品,但写作时他会“用西班牙语来修正英语文字”。道夫曼总是用另一种语言来修改润色自己的草稿。他觉得自己并不是二元语言使用者,而是“双重单一语言使用者”。“当我用西班牙语写作时,体内的英语就在指引着我。”

道夫曼最令人佩服的一点大概就是用非母语写作了。这类作家还包括康拉德、博纳科夫、阿契贝和李欧诺拉·卡灵顿(Leonora Carrington)。和小组中的其他人一样,道夫曼不仅用英语写作,更用上了无可挑剔的漂亮的散文体裁。
像海明威早期的作品一样,道夫曼的语言清晰明了,简洁克制;像卡夫卡和奥斯特一样,书中的意象既强烈有力,又怪异可怕,仿佛抽离了现实。“我笔下的人物没有面容,”他说,“他们都是幽灵和幻影。”这可能是因为道夫曼描写的都是已经故去的人,讲述的都是早已发生的旧事。《达尔文的幽灵》以一个关于种族暴乱的短故事开篇,故事基于历史事实。但最终这本小说却变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样子。你得紧紧抓住故事的线索,跟着人物的脚步,道夫曼提醒读者,“不然你会付出代价的。
暴政和独裁是道夫曼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意象。特朗普自然是无法绕开的一个话题。道夫曼也就此展开了话匣子。在他的长篇文章《如何解读唐纳德·特朗普》(How to read Donald Trump)中,道夫曼将特朗普和唐老鸭联系起来(道夫曼早年写过一部作品《如何解读唐老鸭》),不论是这只黄色的迪士尼动物还是总统特朗普,在书中都没有得到很高的评价。“很显然,特朗普为许多人熟知,但他对我来说则有些特别,令人痛苦。因为这把我带回了过去。”道夫曼指的是皮诺切特的军政府统治。“美国人民原来是有尊严的。”道夫曼说道,但现在妥协了。
“在这片土地上,威权主义正在抬头,愤怒之火也开始燃烧。这个国家没有能力正视自己的过去,这点也体现在特朗普和他的执政之下,”道夫曼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状态。我的推断可能不正确,但我毕竟也见证过民主制度的土崩瓦解。”
道夫曼说,如果继续任这些趋势蔓延发展,美国可能“很快就会陷入专制制度”,然而他并不希望特朗普被弹劾。“我希望他被那些将他送进白宫的美国人民推倒。”我们要认识到特朗普主义的真正根源,而不是简单的痛斥和抨击。“他不是无缘无故走上权力顶峰的,特朗普能走到今天,根源就是美国性格和整个美国历史。”
阿瑞尔·道夫曼有着演员的人格魅力,作家的不羁的灵魂,也像异见人士一样激情澎湃渴望正义。但他更是一个安静的顾家男子。每天他要进行两次阅读,不管是旧书还是新书,不管是小说还是非虚构,他总是和妻子坐在一起,读着同一本书。托马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道夫曼说这几乎成了他的宗教仪式。安赫利卡是他第一个也是最信任的编辑,道夫曼说:“她是我大树的土壤。”
(翻译:马昕)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