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教育是国家全面危机的副产品。虽然洋务运动时期也曾培养少量专门人才来了解、掌握西方技术,但直至甲午战败,才第一次促使中国人真正着手革新教育体制。战场上的惨败,以无比直观而鲜明的方式敲响了传统教育的丧钟:既然它无法退虏送穷,那么要除弊救亡,就必须引入现代教育理念来培养更能适应激烈国际竞争的人才。这便是为什么梁启超1902年撰述《论教育当定宗旨》时作此断言:“吾国自经甲午之难,教育之论始萌蘖焉。”
由于从一开始就是在这样急迫的局势下展开,同时又带有明确的功利性目的,当时“新教育”的推动因而呈现出急骤无比的面目。连废除科举这样的大事也无暇顾及社会长远后果,新学堂的建立与旧私塾的废除更屡屡以国家政令的方式强制推行——因为在当时人看来,这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教育问题而已,而是最为根本的救亡举措,因而全社会和国家意志都有强大的动力促成此事。1904年就有人说过,“现在的新党,没有一个不讲教育的,也没有一个不讲教育普及的。”事实上,即便是那些守旧派都从不质疑“教育是强国的根本”,他们争论的只不过是哪一种教育而已。
对这一段新旧交替时代的历史,已有很多研究,不过着眼点大多是落在“教育史”或对社会影响这样的层面。作为社会学者,应星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略有不同:他用一个社会学术语“场域”来描述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的深远意义。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社会支配关系赖以不断再生产”的机制,在这一功能上,现代教育与传统的科举制度不无相似之处。这给教育赋予了远远超出“教育”本身的意味,事实上,它不仅创造了新的学术制度、新的社会精英、新的政治理念和组织,甚至还参与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传统时代的中国,教育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传授专业知识本身,而是“做人”。正如张德胜在《儒家伦理与社会秩序》中所说的,孔子所希望培育的,是合乎儒家社会规范的“君子”。个人修养(更别提专业知识)不是孔子的终极目标,而是确立社会秩序的手段。不过,孔子也留下一份无人质疑的遗产:要重振一个衰败的社会,教育是最根本的拯救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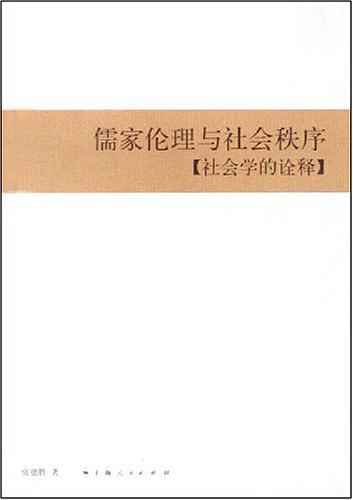
应星基于对晚清士人的分析,也已看出“所谓‘新教育’的实质在于政与学的关系重构”。不过,他认为“传统教育的重心放在为统治者提供优秀人才上”,这一理解恐怕是相当狭隘的。他似乎有一种将“传统教育”与“科举”等同的倾向,但即便是科举制,其实对大部分民众而言也是一种自我实现(更确切地说是为家族)的渠道——无数族谱家规中都有诸如“兴文教以振家声”这样的话,对沉浸在这般祖训中的读书人来说,光宗耀祖可是远比“治国平天下”更强大而直接的驱动力。

晚清政局的危亡改变了这一意识。受教育不再是一部分士人的职责,而成了全民义务;受教育的目的也不仅仅只是为了“丕振家声”或个人修养,而是为了国家。“教育”与“强国”的关联被看作是毋庸置疑的“天演之公例”,并且隐藏了这样一层意味:国民接受现代教育后,理应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其对象由“家”扩大成了“国”。
然而,既然新教育场域会导致社会支配关系的结构性重组,那它势必带来极为深远的冲击。在中国近代史上屡屡出现这样一种情形:一支以全新组织方式和技术配置的军队组成后,便会成为新的政治权力中心。无论是曾国藩的湘军、袁世凯的小站练兵还是国民党的黄埔军校,都证明了这一点。教育作为一个场域,道理类似,只是其影响更隐蔽而深远,因而以我们的后见之明看来,当时的主政者显然未充分料见废除科举、创设新学堂而废私塾、改革新教材等一系列施政措施的后果。
这也是变革年代反复出现的情形:一项新措施的推行,产生了不可控制、乃至事与愿违的结果。对晚清的主政者来说,从科举制到现代教育制度,仅仅是国家想培养的人才不同了,但“取士”的目的并无变化——这就好比李鸿章的淮军已在甲午战争中失败,那就得练新军来适应新的战争条件,仅此而已。正因此,晚清温州士人张棡对新学生的革命倾向颇为疑惑。“答案是:这已经不是‘士习’这样的道德问题,而是新式学生试图以更具主体性的姿态来变革中国的‘反体制冲动’。”
科举/私塾的废除、新学堂的兴起,使得传统“士”阶层失去了依凭,新式学生势必作为新的精英阶层崛起而掌握话语权。应星在书中注意到,不同学校之间的环境有相当大的差异,当时师范学校比省立中学的学生更激进,原因就在于师范学校“生源多是来自贫寒之家的优秀学子,毕业出路大多是回乡当小学教师,他们既对个人能力有优越感,又易生不平感,因此更易走上改造旧社会的革命道路。”究其实质,恐怕正是因为原先的科举制偏重皇权与士绅荣身之间的纽带,但新式教育则转向了更抽象的国家——但问题在于,同样是为国,解读国家利益的方式却五花八门,用当时的话说,到底是救天下、救中国还是救大清?新式学生并不是驯顺的工具,在他们看来,晚清统治者本身就是“救中国”的最大阻碍之一。
新式学堂是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传统的私塾多在乡间,且极其分散,每所常常不过三五个学生;但新学堂却率先在城市兴起,大量年轻人群聚在这样的校园里接受新思想,又有机会密切互动,新型社团组织的活跃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由于旧式精英衰败所造成的权力真空,年轻人遂得以获得不成比例的话语权。江西保守士人胡思敬在辛亥革命后发现,省城南昌“客官排斥殆尽,老成人亦遁去,不知所之。任事各员自都督以下一非军人即洋学生,鲜有年过三十者”。应星对当时南昌几所中学的分析也表明:新式学校正是新型政党组织诞生的温床。
和传统的革命史思路不同,应星主张,像“改造社”这样以学缘为基础的新型社团组织,在最初诞生时其实仍嵌入在传统的血缘、地缘社会关系中,领袖人物往往在亲友、同乡中发展革命组织。此外,他还认为这些组织者之所以能超越狭隘的地域、学校关系,形成广泛的组织网络,是因他们大多是世家子弟,因而拥有较多社会资源。这一分析路径不无启发,但也无形中更多强调了外归因,淡化了组织者的个人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也遗漏了一点:这些基于抽象意识形态的社会政治组织之所以能兴起,也是因为现代教育的环境和理念都潜移默化地让年轻一代从宗法社会中脱嵌出来,他们成了具有独立自我意识的个人。新教育体制终于创造出了新社会所需要的新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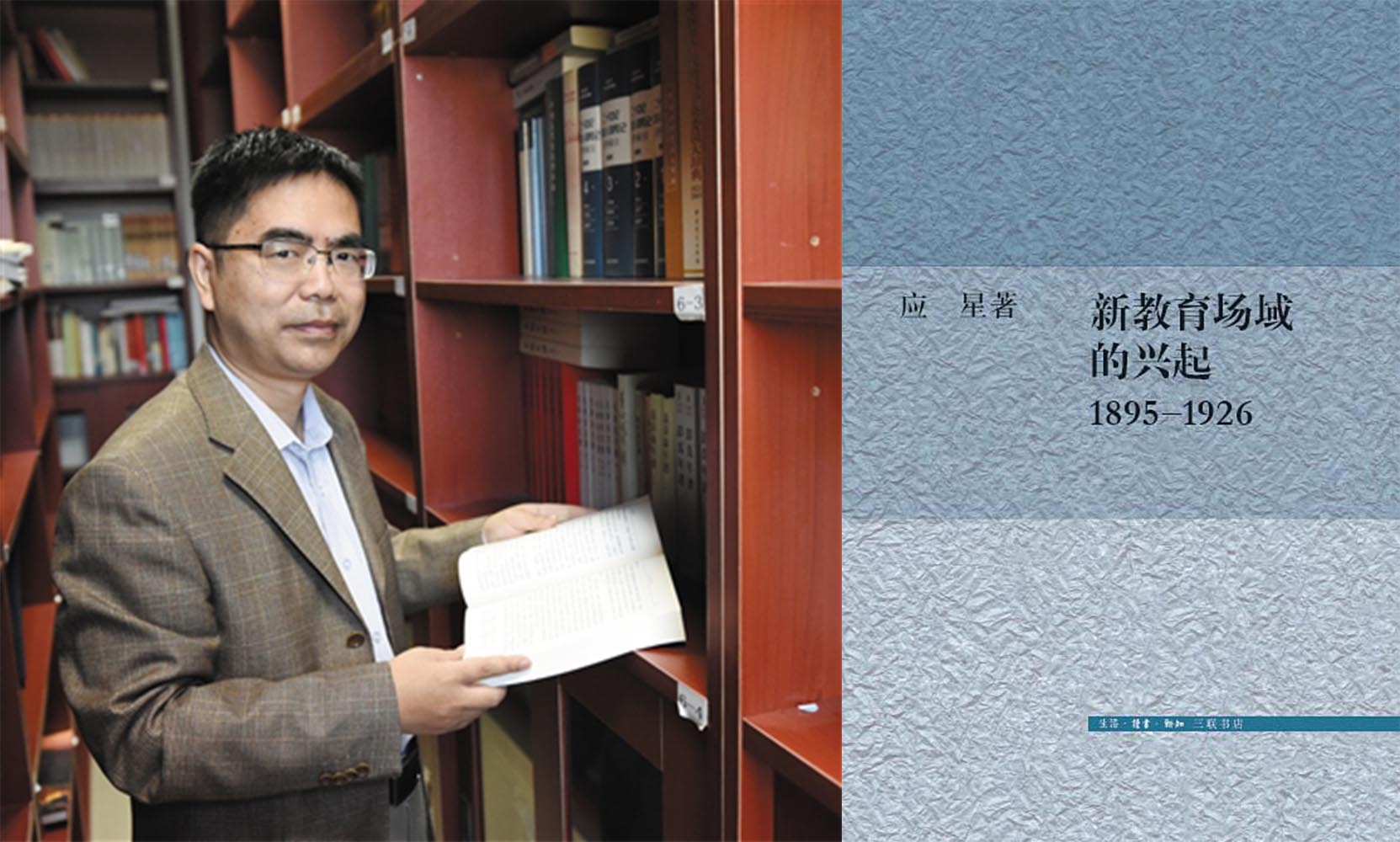
以新容旧
这样的时代背景,也可以让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教育的命运:它从诞生之初就隐含着为新的民族国家创造新人的政治使命,因而很难独立于此。换言之,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教育太重要,因而不仅仅是教育家的事。在1861年意大利初步统一之际,政治家阿泽利奥曾有一句名言:“我们已经创造了意大利,现在我们必须创造意大利人了。”20世纪初的中国面临同样的使命,而最直接的途径就是通过政治动员和现代教育来完成。
不过,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也使得人们得以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创设新型教育体制的自主权。蔡元培是理解这段历史的最关键人物:一方面,他在民国政府成立之初即受命为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主持制定《大学令》和《中学令》,强调各级学校是塑造“健全国民”的所在;另一面,他坚持现代教育是一个独立的专门领域,不应受政治的过度干预。他主张废止祀孔读经、实行男女同校——说到底,都是因为他觉得这都是“新国民”养成的必要步骤,其教育理念隐含着现实政治的关怀是毋庸置疑的;但他又并不希望教育直接为政治服务,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要重振中国的衰弱,需要的是一套能培育现代学术的制度保障。
这种强调专业化的现代主义,与中国传统理念大异其趣,恐怕与他此前四年的留德经历密不可分。在1916年受命主持北京大学之后,他随即将这套理念付诸实施:清退那些把上大学理解为升官发财途径的学生,将大学打造成“研究学问”的专门场所。在此值得注意的是,他完全改变了中国传统上“学问”和“教育”的含义,它们不再是为了塑造符合儒家社会秩序的规范,而是为了激发研究的兴趣,以期获得突破前人的学术成果。换言之,这里说的“学问”类似于现代体育那样不断打破纪录的动态追求。
为此,就必须要推动学科的专业化和大学教师的专职化,因为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就是专业化,如不专精,就无法在科研学术上取得最前沿的进展。他立下的“官吏不得为专任教师”这一条,封闭了学生毕业后通过官师援引去做官的渠道,斩断了教师与官场的连接;不仅如此,他还将商科逐出北大——也就是说,他希望使大学与政治和实业都脱钩,使大学成为一个独立从事学术研究的特殊机构。这个新的场域从以往的政治场域中脱嵌出来,按学术自身的发展规律,培养具有工具理性的现代专业人才。
这其实是极难做到的。从当时的情形来看,北大是全国的特例,而北大能保持自己的独立办学方针,也是靠着蔡元培一次次不惜以辞职来威胁,这极大地依靠他个人的威望和行动,说到底仍然没有什么制度化的保障,能确保他所提倡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即便在他去职之后还能得到贯彻。在此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蔡元培的这种理念其实深受德国学术传统影响,但却很难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中国。德国的学术传统强调学术与政治分离,相信政治是一个有着自身逻辑的不同实践领域,而教育的根本就是“把自己的事做好”;蔡元培当然也知道中国一贯以来完全相反,学与政密不可分,他极有可能认为,这正是中国学术无法达到专精的弊病所在。

在我看来,只有在这一点上,我们才能理解蔡元培提出的“兼容并包”理念。因为如果学术是一个独立的实践领域,那它所需要在意的,就仅仅是学术上的发展本身而已,不必去管政治立场上的新旧。然而民国初年的中国却是新旧之争极其激烈的时代,连温和的胡适都不太能理解蔡元培这一主张,因为在胡适看来,北大应当成为教育革新的基地,而不应存在新旧并立的现象。但值得补充的是,蔡元培的主张在本质上其实也是以“新”为主体来“容”旧,而非新旧混杂,更不是“以旧容新”。换言之,无人相信“新”仅仅是对“旧”的补足,区别之处只在于他们是否还相信“旧”仍有其价值罢了。
虽然一代代后人都不时会重新召唤“兼容并包”,但现实是:这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是一种受挫的理想。这需要以教育独立为根本,而在此后政治影响日渐加深之下,无论是外部环境还是内部师生的理念,都使得这不再可能;学术的专业化尽管在推进,但显而易见的是,晚清民初无论是政治还是学术,都是以“新”激烈排斥“旧”的方式展开的,那些声称要继承蔡元培思想的后来人,大多连“以新容旧”也做不到。五四运动便是空前激烈的以“新”斥“旧”的社会革命,但这样的激进化有其代价:打破了传统束缚的“新人”们,对自己新获得的独立茫然无措,到最后重新嵌入组织化的社会,新教育场域就此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