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叙利亚小男孩阿兰·库尔蒂(Alan Kurdi)的尸体被冲到了土耳其的海岸上。他只有三岁,身上穿着红色T恤和蓝色短裤。今年九月,距离这件事的发生就整整三年了。当时,他的照片占据了欧洲各大新闻报纸的头条,并促使各国政治家正视难民问题。英国《太阳报》曾将此次问题称为“自二战以来最大的危机”。这张照片爆出之后,人们对难民的同情陡升,明显超过了厌恶和漠视,这或许是近年来唯一一次出现这种现象。
在这张照片持续曝光的一个月,欧洲各国政府都强烈地感觉到,他们迫切需要一种不同以往的处理办法;在一些城市内,人们高举着“欢迎难民来到这里”的横幅。然而,同年12月,巴黎恐怖袭击便发生了,人们对于“移民”的态度再一次恶化。2016年,据各大新闻媒体报道,在德国城市中,许多拥有“北非面孔”的年轻群体针对女性实施性侵,这使得公众对难民的抵制拥有了合理正当的理由。在散布谣言者的精心计算下,欧盟举行了公投。武装边境成为了一项重要的、被神化的议题;故意为“外来者”制造“充满恶意的环境”,成为了一项拥有无上荣光的政治议程。阿兰的尸体被发现之后的24个月,有8500人在穿过地中海,前往更加安全的地方时淹死或失踪。如果不是因为意大利海警的救援,死亡人数可能会更高。今年,又有同样数量的人葬身地中海,但是,这些图片再没有成为头条新闻。
如今仍有无数的难民漂泊不定,这些丧生大海的人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英国独立党党魁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曾制作了一份海报,名为“承受的极限”,将难民描绘为千篇一律、数量庞大的军队。奈杰尔·法拉奇还与海报进行了合影。这幅海报传达的态度残忍无情,但有一点是正确的——那就是难民数量确实十分庞大。在阿兰去世的时候,世界上的流离失所者比二战之后的还要多:一共有6500万——几乎和英国人口数相同,他们甚至能够组成一个漂泊中的国家。这些人引发了许多问题,但是,一个中心的问题是:如何让其他人了解这些难民的生活故事呢?如果没有阿兰的照片,我们应该如何激发人们,通过集体的力量,为那些陌生人提供一些帮助呢?
以下三本书都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并且都给出了不同的回答。阮越清(Viet Thanh Nguyen)追溯了近代历史的案例,讲述了移民浪潮和同化融合是合乎自然的事情,并非历史上的异常现象。他认为,文化就像个体一样,其生命力也取决于其创新性和开放性。他提出,最后抵达的人总是最努力工作、创造力最为强大、想象力最为丰富的人——因为这是他们的生命所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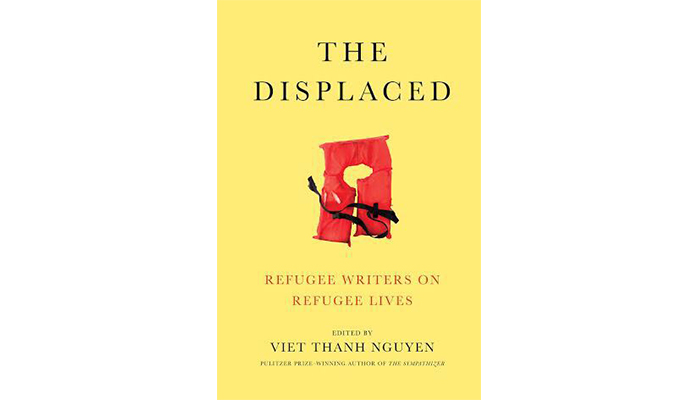
[美] 阮越清 著
阮越清邀请了一些其他作家谈论他们的故事。与他们一样,阮越清也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在成为作家之前,也是一位难民。1975年,在他四岁的时候,他和父母便来到美国。当时的他体会到了步行184公里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尽管他如今已经不太记得了)。他曾看到空降兵的尸体挂在路旁的树上;看到他的父母努力登上一艘船,而其他人却被枪杀;看到他们被关岛、菲律宾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军队视为“异类”;看到他们最终在圣何塞安顿下来。在这里,他的父母开了一家杂货店。但是,他们曾好几次被持枪者威胁,还曾被枪击中过一次;最后,他们还被自己所帮助过的社区所胁迫。这个社区利用硅谷企业所交的税,建立了一座全新的市政厅,而这些硅谷企业几乎都是由企业家移民及其后代所开办的。
一路走来,阮越清的父母积攒了足够的钱,送他去读大学。从西贡逃离出来已经40年了,如今,他已经是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比较文学系的主任。他的第一部小说《同情者》获得了普利策奖。去年,他还获得了麦克阿瑟天才奖。

他的新书里还包括一些其他作家的人生故事。这些作家也曾一度是难民——玛琳娜·柳薇卡(Marina Lewycka)出生在乌克兰的难民营当中,后来定居在英国。亚历山大·黑蒙(Aleksandar Hemon)来自波斯尼亚,现在定居在芝加哥。蒂娜·纳耶(Dina Nayeri)出生在伊朗,在美国长大,如今居住在英国。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许多作家的故事。这些故事提出了一个我认为大家都应该懂得的道理:走得最远的人总会拥有最深刻的洞察力。
这些故事非常美丽,但也经常会令人感到气愤不已。这些故事表明,即便在最为残酷的难民政策之下,同情和人性仍然可能存在。和如今6500万难民的故事不同,书中的这些故事都是幸存者的故事——他们最终幸福地定居下来,并且做出了一番成就,虽然耽搁了一代人。阮越清提醒我们,封闭边界是我们所做出的一项选择,并非是历史规定。每个民族都会在某些时刻认为:“我们拥有欢迎他人、给予陌生人衣物、给予饥饿者食物的能力,这样一来,我们就做到了最好的自己。”在大部分的时刻,我们都铭记着,正义不同于法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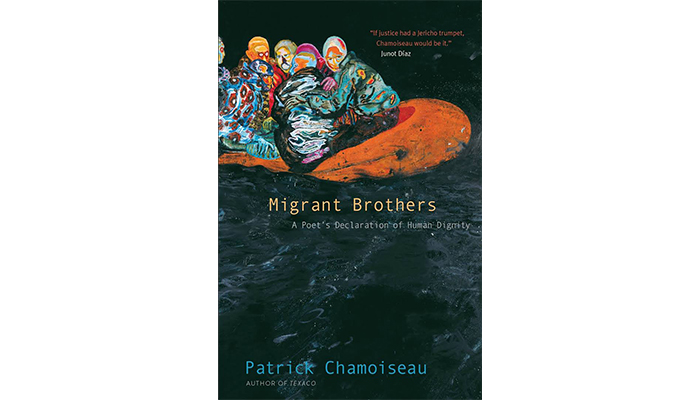
帕特里克·夏莫瓦佐 著
从这个角度来看,改变这种循环,解决“移民问题”,需要思想上的长久转变,而非是政策上的短暂扭转。帕特里克·夏莫瓦佐(Patrick Chamoiseau)出生于马提尼克,在法国长大,之后他又回到了马提尼克这个小岛上。他使用的是克里奥尔化的法语。他的书籍《移民兄弟》(Migrant Brothers)短小精悍,却又富有诗意。这本书是他根据自己对“数百人的了解所写出来的”,“这些人穿越了沙漠、海洋、墙壁、铁丝网、检查点,在噩梦一样的集中营里存活了下来,却倒在了巴黎警察的暴力之下。”夏莫瓦佐试图寻找一种思维框架,来扭转我们的意识。他主张发展一种 “全球性的人性”,他支持“相关的生态系统”、“全球性的感情状态”、“边界的开放灵魂”。他的这种抽象的使命真诚深切,意义重大,但是,你会感觉到,这本书末尾的这句话似乎又在宣告这种状态难以产生:“关系想象使得全球性成为意识领域,而后者又可以在没有任何防卫的情况下,开启水深火热的冒险征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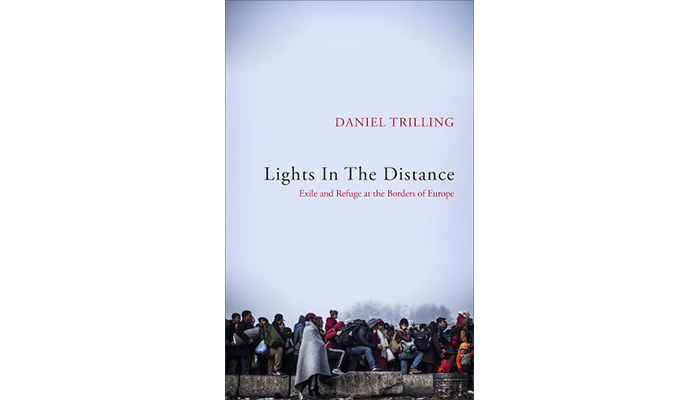
[英]丹尼尔·特里林 著
虽然我们所期待的意识觉醒正在发生,但是越来越多的人依然生活在监禁和混乱当中。记者丹尼尔·特里林(Daniel Trilling)是一位英国作家,他在这些问题上独具慧眼,采取了一种更为直接的办法,让“全球性成为意识的领域”。
经过实地探访和细致研究,他写出了《远处的灯光》(Lights in the Distance),报道了那些被滞留在欧洲边缘的人们。帕特里克·金斯利(Patrick Kingsley)的作品《新奥德赛》和Charlotte McDonald-Gibson的作品《抛弃》也是从这个角度去描写的。特里林在这二人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该类别。尽管特里林非常了解文中的故事,他却不想在书中发表自己的个人观点。他想让读者尽可能地近距离了解到那些人的真实情况,那些人努力地来到法国加来、西西里的卡塔尼亚、伦敦、雅典,却发现人们都在谴责他们占据了别人的生存空间。他在书中描写了一百多个细节,讲述了难民藏在夜晚行驶于高速公路的卡车底部;讲述了他们是如何产生出这种不顾一切的想法;当没完没了地被“检疫隔离”时,家人是如何存活和死亡;他们如何争取身为人的地位,如何无法失去工作……这本书讲述了如何在无穷无尽的绝望之中保留那一点点的希望。
特里林是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他的祖母曾两度成为难民,第一次是逃离俄罗斯,第二次是逃离纳粹德国。1939年,特蕾莎攥着唯一的一本书抵达了伦敦,这本书是瓦萨里的《艺苑名人传》。她努力地活到了94岁。特里林认为,她之所以会找到避难所,会受到接纳,不是因为政府,而是因为公众给政府施加的压力。他之所以举这个例子,不仅是抗议移民政策的军事化,也是在抗议“灾难的等级制”——这种观点蔓延在关于人权的讨论当中,也是在抗议人们一直在关注“经济效益”,却对那些拥有真实经历的人视而不见。
和其他人一样,特里林的这本书也并非全部都是充满希望的。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年代,高墙正在缓缓筑起,而不是逐渐消失。1990年,只有15个国家将边境用墙或栅栏围起来。2016年的时候,这个数字上升到了70个。在这本书的末尾,作者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我们也应问问自己:我们为什么要设定这些条件?管控难民的行动能带来什么利益?冷酷地对待移民的国家,会不会也会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国民?
(翻译:尉艳华)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