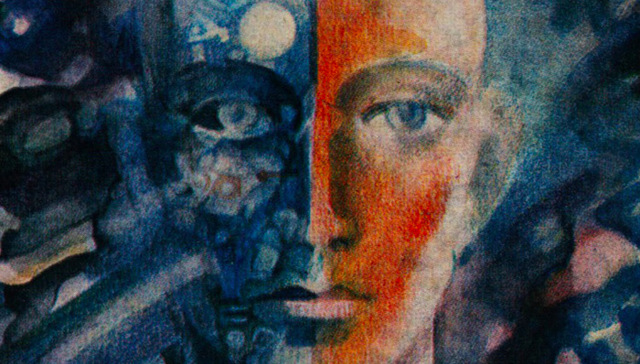这份警方调查报告恐怕会令最有经验的侦探也一头雾水:一位著名作家在南达科塔州食客众多的餐馆里遇害,武器竟只是一个简单的拥抱。凶手似乎没有动机,看起来对自己的行动心烦意乱。这样奇异的案件可能在美国本地报纸的凶杀报道专栏都看不到,它来自1980年代早期保加利亚的科幻小说。解释也变得更合逻辑了:凶手其实是个机器人。
在保加利亚作为共产主义国家的最后二十年里,科幻小说大为盛行。按照人均比例计算,该国也是机器人法则的最大生产国,作为对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机器人三定律”的补充,保加利亚人提出了另外两条定律和96条讽刺性规则。以Nikola Kesarovski(上述机器人凶杀案的作者)和Lyuben Dilov为代表的作家,试图探索人与机器、人脑与电脑之间的边界问题。他们文学作品里呈现的焦虑情绪,反映出一个被科技和控制论压制的社会。
计算机革命带来的确定性,便是工业社会正处于变化之中,甚至将会被终结。正如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1973年写的那样,新式社会中“最重要的不是简单粗暴的肌肉力量或者精力,而是信息”,新式专业人员将要生产的是无形产品。
信息看重知识、智力以及人类的创造力。这种新秩序不仅会改变发达国家的经济形势,就连如何在这种秩序下成为合格劳动者的核心要素也被改变,广义来说,这是在思考机器所构成世界里的个体。2004年,英国社会学家弗兰克·韦伯斯特(Frank Webster)确切描述了这种改变的具体含义,他指出,新人类的输出在“形象、关系和感知方面都不一样了”,也就意味着人类的自我形象不同以往——不再是体力劳动者,而要与思考工具和数字屏幕合作共生。
当时,东欧的共产党也在努力克服这一新问题。他们相信:无产阶级社会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科技为劳动者造福。资本主义信息社会让劳动者被迫与自身劳动力进一步分离,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但社会主义信息社会却能帮助人类摆脱苦力束缚,解放创造能力。就像卡尔·马克思在1845年所说的,人们可以“在清晨狩猎,晚餐后指点江山”。但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及生活其中的知识分子,却已预见到许多现如今我们依然挥之不去的焦虑:在一个不需要人力劳动、思考由机器进行的社会里,人类能够做些什么呢?
保加利亚能够滋生这些想法以及更加激烈的争论,一点都不奇怪。巴尔干半岛直到1980年代都可称得上是东欧集团的“硅谷”,许多生产处理器、硬盘、软驱和工业机器人的前沿企业扎根于此。保加利亚又被叫做“巴尔干的日本”,生产着东欧集团将近一半的计算机设施和周边设备。Kesarovski本人就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数学家,有着多年电子产业工作经验。在这个总人口刚超过八百万的国家里,就有20多万人从事电子生产业。保加利亚执政党也的确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小国改造为信息社会的先锋。

回溯到1944年,苏联红军席卷多瑙河畔,保加利亚共产主义者也在索菲亚夺取政权之时,这个国家还主要是个农业生产国,遍布欧洲的德军尤其钟爱这里的烟草。随着香烟逐渐流入苏联军队和公民的口袋里,社会也从乡野转向城市,数百万人涌入新建造的工人宿舍和厂房。到1960年代,保加利亚已经彻底被工业化所改造。尽管开始出现住房紧缺、城市基础设施不足等问题,却还不够掩盖社会主义现代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光芒。这个生产机器、汽车与轮船的社会被乐观主义急速推动。保加利亚共产党在谋求更多经济利润时,开始将电子工业视作未来生产的焦点。当时,整个东欧都在制造计算机和电子元件,但却没有国家真正实现规模化生产,产业发展逐渐落到了资本主义竞争对手的后面。
此时,保加利亚展开了一系列运作,与日本企业(如富士通等)保持紧密联系,频繁启用工业间谍,在一众社会主义盟友国中独占鳌头。很快,原本主要生产烟草的小镇开始为数百万客户提供计算机。
尽管不够完美,零碎散漫,自动化生产还是逐步在工厂车间、仓库货栈乃至办公室实施开来。从1980年代起,保加利亚开始生产机器人和私人电脑,越来越多的体力工作由这些机器人完成,也有越来越多的办公室和服务变得计算机化。保加利亚共产党自信地宣称,将通过“自动化”来建立起共产主义。工厂的计算机能够提供准确的经济信息,将信息反馈给首都索菲亚,以便做出更为确切与完美的发展计划。借助于自动化的数据收集、战略决策以及行政管理,诸如短缺、坏账和盗窃之类的问题都得以解决。而这一切都依赖于一个覆盖保加利亚全国的广大的计算机网络,它甚至能将集中化程度最低的小农场与首都的中央电脑联结起来。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开始出炉类似的规划,其中尤以苏联的“全国自动化网络”(OGAS)计划为代表。得益于完美的反馈,既定计划得以施行,保加利亚社会主义如同一个完整的有机体运转起来。
保加利亚共产党又进一步指出,随着计算机和机器人接管过易犯错的工人的工作,产品质量也会得到提升。“机器人自动化让产品质量从客观上得到了保障。不再被人类身体和心理因素所左右,而由机器的程序和设定能力所决定。”
然而,保加利亚新技术的工程师、控制论专家、拥护者们,却对这种表述传达的意味忧心忡忡。在索菲亚的技术控制论和机器人技术研究所这样的象牙塔里,科研者写下了诸多关于机器人运动、图像识别、算法设计相关的详细文献。为了进一步优化人机界面接口,他们建立实验室,反复实验——比如帮助办公室白领眼疲劳最小化的办公室设计,再比如未来人类与机器视线的融合利用。人类被越来越多的看作电子人,人类和被人类操控甚至发号施令的机器混到了一起。
科技骨干担负着创造这样的半电子人及相关理论的任务,他们也开始担心此种工作对于人类总体上的影响。争论不再限于实验室内,更出现在哲学期刊和流行科学杂志上,比如深受青少年和成年人喜爱的《宇宙与轨道》(Cosmos and Orbit)。保加利亚的读者也开始思考:人性将在新时代走向何方。哲学家Mityu Yankov认为,人之所以与动物不同,就是因为人类具备改变和塑造自然的能力。成千上万年以来,人类都在依靠体力与肌肉完成这项工作。但工业革命却让人类的本性开始发生变化,并在信息时代达到顶峰,人不再是劳动者,而是“统治者”,是自然的主人,生产的方式也不再是机器或肌肉,而是人的大脑。
由此,人类的工作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产,而是创造。当时,保加利亚的文化部长、国家元首的女儿Lyudmila Zhivkova对于通神学、东方神秘主义和印度哲学颇感兴趣,她在美学理想哲学指引下大力倡导社会对多才多艺、真正具有创造性的“新人类”的需要。
此时,计算机的用处就在于帮助“新人类”利用好现代社会的过载信息,利用数世纪积攒下来的知识将其改造为“新文艺复兴”时代人。科技释放出的力量将使人性上升至另一高度,达到更高的道德责任感。哲学家Victor Stoytchev认为,控制论下的人类应当尽力成为萨列里(Salieri),而非莫扎特(Mozart)。虽然奥地利的莫扎特的确是十亿分之一的天生奇才,但他的意大利对手却以一种坚定不移的固定套式实现了同等级竞争,他将宏大的任务拆解成碎小的细节,凭借不屈不挠的毅力与不辞辛劳的汗水,将一个一个的音符编织成多声部的天籁之音。萨列里展现出了获取创造力的真正途径,而非等待变幻无常的自然的馈赠。在Stoytchev看来,他并不悲哀,而是新形式艺术和完美作品的缔造者——通过劳动力实现的完美,通过选择正确信息实现的通达。如果他能够活在这个时代,必将成为真正的天才。
这些语言显示出一种与现实不符的内在乐观主义。随着计算机进驻工作场所,心理学家察觉到劳动者队伍中持续增长的焦虑情绪。这些机器不仅没能促进创造力,反而形成了压制。伴随焦虑而来的心理压力问题异常突出。1980年代末期出现的报告指出,大部分人正越来越依赖自己所恐惧、备受折磨的机器,而那些喜爱新式工具的人们又陷入了理想化世界,失去了真实感。从1984年起,保加利亚的学生必须上义务性计算机课,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和工程师开始怀疑其影响。随着“第二识字能力”成为进入新世界的钥匙,难道不是也有更多的孩子沉迷上瘾了吗?
与此同时,孩子们阅读到更多探讨同样问题的科幻故事。Dilov是保加利亚科幻小说优秀作者之一,凭借1974年作品《伊卡洛斯之路》(The Road of Icarus)为人所知。人类开始走向小行星挖造而成的宇宙飞船,这里成为新世代人类的家园,这代人的目的只有一个:探索宇宙。小说主人公Zenon Belov是第一个诞生在伊卡洛斯星球上的孩子,是真正的外星公民。
故事的转折点出现在一位创造出半机械人的科学家被审判时,他设计的这个半机械人能够玩耍和学习,确信是人类对游戏的沉迷才让我们能够成长为独立个体。但这样的实验是被严令禁止的,机器人只能成为人类的助手,而非人类的模仿者。更可怕的是,为了尝试克隆,这个半机械人的脑电波功能与创造它的科学家完全一致。审判最后,半机械人被处死,科学家被冷冻。伊卡洛斯公民开始讨论是否应允许改变这些严苛的规则。
这本书对科学家制定的规则提出了警告。这些规则或许有利于保持正常运转,却经常让社会难以实现必需的前进与飞跃。伊卡洛斯翱翔宇宙之际,这里的人们并没有产生实质性进步,直到少数局外人带来改变,这包括原本就诞生在星球上的人们,他们对自己生活里的新奇事物并不满足。
科技焦虑依然没有消退,在充斥着机器的社会里,人究竟是什么?作为对阿西莫夫“机器人三定律”的补充,Dilov制定出机器人第四定律:机器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被认定为机器。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是因为有机器人专家试图赋予机器人更多契合人性的功能和外观,通常会模仿动物或昆虫的形态。Zenon从很小时候就见证了机器人与人类的互动,也让他得以从外部视角审视机器,这种文学构想也逐步毁坏着我们对依赖着的机器的信任。人类需要与机器人划清界限,需要确认自己始终握有控制权,不会被机器欺骗。对于Dilov来说,焦虑源自人性的限制,至少在这个时代,人类还难以视机器人为同类。
Kesarovski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科普作家,经常为孩子们撰写计算机使用指南,还会创作文章,赞美信息科技是未来问题的解决手段。这种想法反映在他的短篇故事里,其中三篇收录在1983年出版的《机器人第五定律》(The Fifth Law of Robotics)文集当中。第一篇里,他将人体视作机器进行探索。一个科学家一直极力搜寻外星人讯息,最后竟在自己的血液细胞里有了发现。在试图解读外星人传达的讯息、理解对方描述的社会形态时,科学家逐渐明白,自己的身体就是一种机器人。Kesarovski对人体镶嵌式机器人的认知表明,他是比Dilov更积极乐观的作家。
Kesarovski对人性的警告也贯穿《机器人第五定律》始终。当小说开始在著名漫画杂志《Duga》上连载时,已经获得了相当广泛的读者群体,年轻人尤其对其钟爱有加。在本文开篇提到的机器人凶杀案里,主人公并不知道自己是机器人,由此违反了阿西莫夫的第一定律(机器人不能伤害人类)和Dilov的第四定律。Kesarovski在其著作里提出的第五定律规定,机器人必须知道自己是机器。随着小说的推进,故事里呈现出一个融合了最优质机器身体和人类心灵的半机械人,他凭借自己的武器掌握了人质。虽然这种《终结者》一般的故事现在听起来如同陈词滥调,但它还是迎来了充满希望的结尾:一位机器人心理学家让Christ回想起自己对Peter说过的话,他可以背叛自己三次,在这个基础上就能够建造自己的教堂了。Kesarovski认为,计算机和机器人会导致危险,但也能带来希望,前提是人们要将其视作机器本身,从机器身上获取力量,从而前进到历史的下一阶段。
保加利亚作者对于创造机器人定律的偏好,又成为了另一位该国作者Lyubomir Nikolov的主题。在他1989年的作品《第一百零一号机器人定律》(The Hundred and First Law of Robotics)里,一位作家被发现在写作时身亡,他笔下的故事讲的是机器人绝不会跌下屋顶。而凶手正是一个不再想听到任何规则的机器人,它最后制定出这样一条终极定律:“任何试图给单纯的机器人制定规则的人,会立刻受到被阿西莫夫全集(200本)砸中脑袋的惩罚。”
保加利亚的机器人令社会深感恐惧,却也意味着未来与希望。人类想要终结无意义的体力劳动,却生产出如今这个自动化世界依然如影随形的焦虑。人类能够做机器人完成不了的什么事情?这个问题我们依然没有答案。但就像Kesarovski那样,或许我们无需如此害怕这个新世界,也无需放弃对更美好、更简单世界的期许。
(翻译:刘欣)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