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文化界受精神分析学之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影响十分深厚。作为20世纪最富争议的思想家之一,弗洛伊德及其作品被阿拉伯文化界一遍又一遍地细细品阅,读者包括小说家、心理学家、老师和学生等。在阿拉伯的文化重镇埃及,弗洛伊德几乎已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著名文艺杂志《阿尔希拉尔》(Al-Hilal)刊登文章,论述了1938年一代埃及学子对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性驱力”等思想的继承与批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曾于1941年空袭埃及,埃及作家Ali Adham当时写了一篇论述弗洛伊德“死亡驱力(阿拉伯语是‘gharizat al-mawt’)”的文章。Adham指出,在战争中,“死亡驱力”意图毁灭的对象从自身转移到他人,我们对他人不仅会产生性驱力,还会有攻击和毁灭的欲望。两年之后,学术界心理学家Yusuf Murad出版了著名畅销读物《治愈心灵》(Healing the Psyche ),意图基于弗洛伊德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创建一个独特的精神分析学派。这本书带领读者走进了这一独特的精神分析学派,教会人们重建“自我”,尤其是对那些曾经受过伤害的人们。
弗洛伊德的影响范围从来不只局限于学术界,他丰富的思想也不只是学院背景之下诞生的产物。1939年,纯文学作家塔哈·侯赛因(Taha Husayn)首次将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翻译成阿拉伯文,这部著作是弗洛伊德思想的奠基石。很快,该著作的两部改编版本也相继问世。在1949年埃及剧作家Tawfiq al-Hakim改编的版本里,这部悲剧的核心冲突从表面事实与隐藏真实之间的冲突,转换成了人与命运之间的抗争,这是极具弗洛伊德色彩的一次解读。但真正将俄狄浦斯之谜鲜活地呈现于阿拉伯读者面前的,还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埃及小说家纳吉布·马哈富兹(Naguib Mahfouz)。
马哈富兹用精彩无比的《幻想》(The Mirage)一书,带领读者进入了主人公Kamil Ruʾba Laz的内心世界——他性格含蓄内敛,深深地迷恋着他的母亲,而且,马哈富兹描述道,这种“迷恋”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范围,成为了一种“具有毁灭性的病态的热爱”。马哈富兹细致地描述了这位年轻人精神上的情结,他的喜悦与痛苦受母亲一颦一蹙、一举一动所影响,他用白日梦去逃离沉闷无味的现实。长此以往,对母亲的迷恋和欲望使他内疚不已,他也无法找到自己的真爱从而步入婚姻,在这样复杂情绪的煎熬之下,有一天他最终找到了自己。这本书影响深远,在1951年,一名埃及中学哲学老师甚至提议,应该推行婚前精神分析学测试,以保证不会有人带着俄狄浦斯情结步入婚姻,导致婚姻与家庭的不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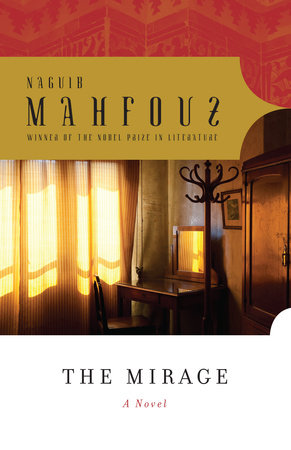
也许,俄狄浦斯情结在埃及最意味深长的一次现身并非出现在小说里,而是在法庭上。20世纪40年代末期,开罗一名犯罪心理学教授默罕默德·法蒂(Muhammad Fathi)热切地将罪犯心理动机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联系起来,尤其是用在那些杀人犯们身上。在一系列广受欢迎的文章中,法蒂指出,精神分析学与犯罪心理学其实是具有统一性的学科。精神分析学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暴力犯罪行为背后罪犯们的行为特征及深层动机,甚至警方的行为动机,更有趣的是,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并理解被弗洛伊德称为“因罪感而犯罪”的一种罪犯。这些人之所以犯罪,是因为他们对于自身无意识的犯罪倾向有着潜在的想要被处置的欲望。先有罪感,而后才有罪行,而非反之。
法蒂还举了各式各样的例子,比如一个单身汉爱上了一位年长的已婚妇女,这种罪感就驱使他最终杀害了她的丈夫。一旦罪行完成,乱伦弑父的潜意识欲望就可以遭到打压和处置。法蒂的理论在埃及掀起了激烈的讨论,学界一些精神分析学者认为,法蒂过于迎合大众心理,对于俄狄浦斯情结进行了过度阐释,俄狄浦斯情结与罪犯心理其实并不具有如此强大的相关性。但无论如何,对于埃及人来说,弗洛伊德的理论思想都是值得一再讨论的。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弗洛伊德的作品被翻译成阿拉伯语引进之前,埃及人以及其它阿拉伯人就已经热衷于研究并讨论弗洛伊德思想了。弗洛伊德作品的早期译者之一Mustafa Ziywar,同时也是巴黎精神分析学会的第一位阿拉伯成员。他自愿为无数有志于从事该领域的埃及精神分析学者提供指导性意见,不管是他们将来会在埃及、法国还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进行发展。Moustapha Safouan是一位杰出的拉康研究专家,同时也是Ziywar的学生,在他的描述里,Ziywar是一位“在向上帝宣誓之前会首先向弗洛伊德宣誓的人”。Ziywar主编了《精神分析学派的创立》(The Foundations of Psychoanalysis)这一系列书籍,20世纪50年代,Ishak Ramzy翻译了这本书介绍精神分析学派的引言部分以及“超越快乐原则(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这一篇,1957年Ziywar翻译了其中弗洛伊德自传研究的部分,1958年Safouan翻译了“梦的阐释”这一部分以及其他弗洛伊德的著名篇章。Ziywar孜孜不倦地翻译和引进弗洛伊德,是为了能让更多人接触他卓越的思想。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甚至在开罗开办了一系列以精神分析为主题的广播谈话节目,讨论与大众息息相关的问题,比如赌博、吸食大麻和抑郁症等。
50年代到60年代期间,这些话题成为了埃及国内的中心议题。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意图打造一个社会福利丰富多样的政治制度。事实上,纳赛尔出身的自由军官集团在1952年成功夺取政权之前,曾经与精神分析理论颇有渊源,他们利用精神分析理论来考察军官和飞行员。其后,随着50年代国家社会学和犯罪学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Sociological and Criminological Research)的建立,社会科学家把社会文化议题纳入了研究范围,由此吸引了一大批精神分析学家。举例来说,1957-1960年与1960-1964年期间,该研究中心分别进行了关于卖淫和大麻使用这两大主题的大规模研究调查,后者是由Ziywar亲自带领研究的。
对于刚独立不久的埃及国内的一部分(绝不是全部)弗洛伊德研究者而言,精神分析已经沦为了一种统治的工具,它可以帮助规避社会学和心理学上的一些缺陷,创建全新的后殖民时期公民主体。而事实上,这种把精神分析学当作创建或改变人类主体性的工具的倾向十分之危险,不仅在埃及,其他一些国家也有这种危险的倾向。这是因为,精神分析学本质上是为了提供一种关于人类享乐途径或目的的深刻认知与批判,无论这种享乐是人类拓宽知识的驱力,还是仅仅让我们变得易于被统治、对社会政治形势更加适应的手段。为了快速重建去殖民化的国家公民主体,一些精神分析学者有时会罔顾精神分析学派道德与哲学上的批判价值,而将自身置于险境。
(翻译:朱雨婷)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