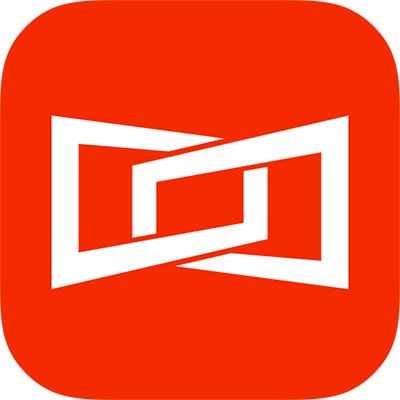作者:邵乐乐
以下是《三声》(微信公号ID:tosansheng)与《河神》导演田里的对话整理:

田里
你是怎么接到《河神》这个项目的?
田里:几年前,工夫影业从天下霸唱那里买了《河神》这个IP,算是提前嗅到了互联网内容的发展趋势。买过来之后就在工夫影业内部做了两年剧本开发。但那时候网剧还没成气候,工夫也没有做网剧的经验。
到了2016年,陈导(工夫影业创始人陈国富)包括公司上下也都觉得,《河神》这个题材可以拍。但如果按照传统的思路,承制给一个电视剧公司或团队比较稳妥,起码制作方面不会出现太大偏差,回报各方面也有预期值。
但是他又隐约觉得不太对,如果真这么做的话,似乎没有意义。不做出点突破和创新,也不太像工夫的性格。总体来说,工夫还是想做出点成绩出来,就试着尝试能不能找到一些敢拼敢闯、想要在某一领域干出点儿事来的年轻团队来做。现在回想起来,陈导这个事赌性挺大的。
但这个事找谁做呢?正好王博学跟陈导他们引荐了我们,工夫也比较信任年轻人,以共同成立子公司的方式来扶持我们,《河神》项目组和闲工夫同时成立。
确定我是导演之前,我只跟陈导见过两次面。第一次见面,陈导说他希望《河神》的气质妖魅一点、邪一点。这跟我想的一样,《河神》肯定不能拍正常了,得哪儿哪儿都不一样。第二次见面,我们做了提报,一边讲一边放参考段落片,后来陶总(陶昆)说那次提报最关键。
对你来说,《河神》的兴奋点在哪里?
田里:说实在的,当时最大的一点就是:有东西拍就不错了,这是最功利、最基础的出发点。因为我们电影学院毕业出来这么多年,能抓到一个叙事型的、可以让你讲故事的机会很少。
我自己也特别嗨《河神》这种类型化明显的片子,喜剧片就特别喜剧,科幻片就特别科幻,恐怖片要特别恐怖,文艺片就文艺到底,一条道走到黑就行了。《河神》这个故事就挺独特的。当时网剧市场也没有特别多的规范,陈导他们只是说这个剧要按照美剧模式做成13集,每集60分钟。
但这个体量在盈利和造势上会比较吃亏。
田里:当时没有想那么多,爱奇艺也还没有介入。因为工夫影业管事的人是搞创作的,对待作品的态度都极其认真要求极高,就跟我们说先按照自己的想法拍,拍完了再卖,只要东西好,肯定有人要。爱奇艺进入这个项目之后,工夫从平台的规格要求和播出模式等方面考虑,决定做成24集,所以开机之前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扩充剧本。
《河神》在改编和原著之间尺度拿捏得很好,你们有自己的方法论么?
田里:方法论就是粉碎性改编。在我看来,所谓的IP改编其实是一个误区,所谓“尊重原著”四个字就是在害人。因为一个作品的群众基础越大,它在群众中的想象就越多元,你就越难满足原著粉的需求,一千个观众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与其这样,还不如找到自己感兴趣的点,找到影视化应该注重的地方,抓到原著粉所谓的精髓,然后放开做。因为其他的考虑都是束缚。
汪监(汪启楠)说过,IP是编剧的敌人。所谓编剧需要的是你的创造性,你自己对人物、对故事结构的理解。如果有现成的东西摆在面前,就是一个手铐,你一定要甩开。
《河神》的原著和剧几乎没有关系,但是天下霸唱提供了一个世界观:民国时期的天津码头文化。所以我一直觉得《河神》是民国传奇,魔幻而飘不起来。它一定是传记,来自某一个有依据根源的评书,或者一个口口相传的老人们讲的故事。它一定是贴地飞行的,不是踩在地上的,也不是飞起来的。这就是天下霸唱给《河神》赋予的最核心的东西,也是我认为《河神》应该抓住的精髓。
所以,“尊重原著”是伪命题,不管是闲工夫还是工夫,都不会被IP捆住手脚,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改编思路。
改剧本的时候,爱奇艺有提什么方面的要求吗?
田里:剧本基本没有,爱奇艺充分信任我们。爱奇艺是专业度很高、沟通成本很低的平台。再加上工夫也比较护犊子,所以总体来说,我们有一个比较宽松的创作环境。平台也就是拍摄期间探探班,陈导和汪监(汪启楠)也探过两次班。
他们探班看什么?
田里:汪监比较关心剧本,陈导会比较专注于现场的情况。他在现场非常认真,戴着耳机听每一句台词,也会一直盯着监视器。他会过去跟演员说,丁卯(《河神》剧中人物)的领结是不是要往上放一放,后面的群众演员表情是不是要多一些。所以他在的时候,进度会慢下来。后期也一样,陈导完全用电影的思路抠得很细,修改意见会精确到镜头,这种具体的指导和意见非常受益。
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人,剧组所有部门都快被我逼疯了。好在摄影、美术、制片这几个大主创都是年轻人,对自我有追求,想干出点事出来,所以也都很配合。
但是更基层的工作人员受不了。他们会说,“我们是来拍电视剧的,结果你这完全是电影的拍法,还有电视剧的进度要求。但我去横店一天挣这么多钱,在你这儿也一样,那你不能这么拍戏。”
整个剧组天天熬大夜,121天发了100天宵夜,70多天都工作到午夜,所以特别苦。松江地区的武行和群演都闻风丧胆,“明天有活,什么戏,《河神》?不去。”我们只能从上海市区和外地调群众演员,反正他们不知道《河神》什么剧。
拍丧尸那场戏,真的特别痛苦。两分多钟的长镜头一拍拍一天,50个武行在现场,脸上需要化妆,嘴里含着血浆,演员真打真受伤,所以拍着拍着镜头里的人就越来越少。一个人化妆需要一个小时,服化组全员上阵也化不过来,我们只能从凌晨一点半开始分批化,化到早上五点半开工,拍摄期间还不停地补,武行和群演都疯了。
这种情况对于制片人常犇来说应该是挺难搞的事情。
田里:肯定是。但我们俩配合挺好的,所有的问题都不会影响到我。所有对于创作层面的不理解和负面情绪,在常犇和每一个部门长那里就被摁住了。
所以相较我而言,常犇更难,他起了很大的作用,把所有事情都摁住了。常犇的理念就是,我永远跟导演站在一条线上,拒绝任何对导演的质疑。这也是有审美的制片人该做的事情。
你们的团队都包括谁?我们看《河神》整个片子调性自成一体,应该是团队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田里:我和常犇,制作总监王博学,还有摄影冯思慕,他也是电影学院的,后来去美国AFI学的摄影,美术老师是电影学院比我们大三届的师哥,作曲跟我们同届,声音指导比我们大一届。这个团队基本上都是上下届的哥们,大家看的片子、喜欢的东西、审美取向上比较一致,所以才会在一个语境下形成有效交流。这也是我们找对了人,团队的力量非常重要。
造型指导袁斌老师是艺术家前辈,袁斌老师从《鬼子来了》到《太阳照常升起》一直在做姜文导演电影的化妆组负责人。老艺术家给《河神》做的造型真的帮了大忙——帮了创作,帮了摄影,甚至帮了演员。
比如,李现(《河神》中郭得友的扮演者)的脏辫对整个角色的气质提升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小神婆的造型也是,紫璇(小神婆的扮演者)说她穿上那身衣服之后,就知道小神婆这个角色应该怎么走路。还有小神婆头上戴的花和鸟巢,这个造型其实很夸张,一般造型师不敢用。我当时看了,第一反应稍微楞了一下,但是仔细想,就得这样。
我跟所有的部门都说,你们要抢。很多人说牛逼的创作是不露声色的,比如最顶级的配乐让你感觉不到配乐。但我不要,我说你们就抢,就拉着观众,让他们看到——这是我拍的画面,这是我置的景,这是我做的造型,这是我配的乐,这是我做的特效。
《河神》主创团队基本都是新人,或者说还在挣扎的人,大家一直都没有遇到特别好的机会,但是也都一直彪着劲儿,在等好的机会和好的合作伙伴。
所以说到《河神》的审美体系,我认为这就是团伙的力量。《河神》遇到的这波主创全对,运气好。这波人凑在一起,一定能够发挥1+1>2的功效,再加上一点点导演的催化,才会有现在的结果。但也谈不上特别满意。
陈导对《河神》满意吗?
田里:谈不上满意,他没有过高的预期,因为剧就是剧。我个人冥冥之中会觉得《河神》会是一个口碑还不错的剧,起码业内人会觉得有意思。但是我们都没有想到观众会这么嗨,豆瓣评分这么高,这确实还挺超出预期的。
陈导对哪些地方不太满意?他的标准是什么?
田里:他没有所谓分门别类的标准,所有的东西都要符合他自己那一个标准。陈导是一个标准极高的人,比如说拍摄的时候,他一定忍受不了影视基地的各种条件——景的大结构不能动,衣服的质感很糙,有的群演特别不会演戏。
一个像陈导那样对作品要求的人坐在现场,他是很难受的,哪儿哪儿都不对——这个门怎么这样?时间怎么这么赶?四天半就要拍一集!他心里没有拍剧的概念,在他看来现场就是妥协。
当然,我们也会通过调色、特效、剪辑的方式在后期做各种调整,但即使这样还是离他平时一贯的创作要求和标准太远了。所以他一直对《河神》没有过高的预期,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也就那样了。所以后来还挺出乎意料的。
《河神》前后,你觉得他对网剧的认知有变化吗?
田里:有,我认为他有变化。以往工夫很保守,也很大胆,一方面创作和理念上很先进,另一方面做作品态度很保守严苛。
在《河神》被市场认可之后,整个公司的战略上会有变化。包括闲工夫、工夫小戏、真言以及后来成立的一拳等子公司,工夫在整个互联网的网生内容市场的布局、投入、思路都变得不一样了。
你不能完全说是因为《河神》之后才这样的,但是《河神》肯定给了他们定心丸——这种创作思路、选择人才的方式是对的。
你自己对网剧会有什么认知上的变化么?
田里:没有。因为我始终没有把网剧单独拎出来看待,所谓的网剧、电影、网大,在我这儿态度都一样。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大家都分得太开了。
但标准的区隔确实是客观存在的,你会有执念说我一定要拍电影么?
田里:我没有,我拍任何东西都是一样的标准。当然,做我们这一行一定都有电影梦,我们在电影学院上了七年学,学的也是电影,也没有哪个课是网剧课,但对待内容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反正我是这样的人,过不了自己这关就是过不了。
以前当然也会遇到无奈,我心里会有一杆秤,比如我知道需要什么样的东西,但人家就是做不到,那怎么办?你也不能说我不拍了,该妥协还是妥协。但是立竿见影,出来的效果肯定不会好。
现在时代好了,机遇好了,整个环境好了,大家也认创作、认内容。我们也遇到了对的团伙,这帮人心里都彪着劲儿,等着碰到各方面都合适的机会。一旦碰到一定不会放过,所以《河神》就成了。
对你来说,没有拍《河神》之前,在电影市场也很难有这种机会么?
田里:很难。我们当年的大环境就是青年导演难,青年导演没机会。但是现在网络平台起来后,年轻人的状况好像完全不一样了,处处都有机会,处处都有商机。
我感觉就是这几年,门槛被降低了一大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帮人一下子都能够出来。以前门槛非常高,即使是我们这样的也够不着,比我们能力低的人更够不着。当门槛下降的时候,很多人有机会迈进来,那我们自然就变成这些人里比较拨尖的。
2008年毕业后,除了期间回电影学院念过书,其他时间你在做什么?
田里:跟组、写剧本,当场记、做副导演,自己也会当导演,拍一些微电影、宣传片、广告,还帮别人拍过一个恐怖片。生活上也没那么苦,更多的苦在认知和创作上,有时候会苦恼什么时候能拍一个自己喜欢的、有发挥空间的东西。
那个时期你印象中的电影市场是什么样的?机会多么?
田里:那个时候新导演真的挺难的。不光是新导演,甚至到现在我一直都觉得导演一个是很尴尬的职业,这种尴尬可能是整个影视体系或者环境的不成熟导致的。电影学院导演系多少年不出导演了?但美术系、文学系有大量的人当导演。后来我毕业论文就想搞清楚导演到底是干吗的。这是一个终极话题,相当于搞清楚电影是什么。
大家经常会用一个词叫“电影感”。到底什么是电影感?我觉得只有电影能传达出来的感受,才能叫电影感。也就是说,你拍这个电影作品,它称之为电影的必要性和唯一性到底有多大。唯一性越大,电影感越强。如果换别的载体也不影响整体表达,那你为什么拍成电影?
电影是一门时空艺术,除非通过电影,否则其他任何形式都不够充分表达那个感觉的,才叫电影感。但是这道门很窄,导演要做的事就是往这道门里面挤,看自己能把那个门打开多大。你开的越大,就越像导演。我认为这是我们作为导演应该毕生追求的那道窄门。
《河神》中你觉得自己有打开一点那道门么?
田里:我在尝试,但我觉得谈不上。《河神》大部分还是在做一个及格线以上或者相对出色的东西,但真的谈不上诉求表达,或者一个导演内心的挣扎。只能说机会来了,我得把握住了,不能辜负了陈导,不能辜负了爱奇艺,人家那么相信我,我不能拍砸了,得拍得故事好看,画面好看。
完成这样东西,从技法上来讲对你们是没有压力的?
田里:也不能说没有压力,只能说我相信我自己能做到。但是确实每天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有很多实际的、客观的困难,没办法,只能克服。因为以前我们没有拍过这么长时间的戏,没有干过这么大的阵仗。
每天深夜,我跟常犇都在房间里发愁——怎么办?明天可能会面临18个从来没有面临过的问题,这18个问题只要其中两个出现了、解决不了了,这个剧组可能就要黄了。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心态更多的不是纠结、不是恐惧,而是你只能想办法。
我们俩经常呈现出一种兴奋状态,就是——刺激,真刺激,感觉肾上腺素在飙,经验值也在飙升,仿佛自己在面临一座山,但是很快就要爬过去了。《河神》真的太难了。
会后怕吗?如果下一步再做类似的重型网剧。
田里:不会。我们经常说,《河神》能拍下来,没有什么戏拍不了了。所以闲工夫接下来一定要拍重型的、类型化明确的、可以给公司打标签的东西。这肯定会越来越难,但乐趣就在于知难而上的过程。
我最喜欢的导演是库布里克。我们老说给导演打标签、给公司打标签,但库布里克特别牛的点就在于他有非常个人化的标签,他拍越战、拍恐怖片、科幻片,拍各种奇奇怪怪的片子,但你看的时候都能感觉到这是库布里克拍的,这是非常高级的一点。诺兰也有这种特性,但是他更偏结构派。
总的来说,这一类导演都会比较偏执,在某些方面永远恪守自己的原则和底线。我没有他们那么偏执,但希望自己能够成为那样的导演。
三声原创内容 转载请联系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