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暂从
法国1959年,戈达尔的第一部故事片《精疲力尽》诞生,于是不明确的新浪潮风格有了“唯一”的风格,树立了戈达尔在新浪潮运动中的角色,出手即明确其在电影界的立场,撼动了固有的电影语法,震惊影史。
新浪潮是由五十年代末的法国发起,而后引领了全世界的电影变革。在这场充满各种错综复杂意义的“新浪潮”中,本应百花齐放的局面,却成了戈达尔的一枝独秀。今天(12月3日)是戈达尔的87岁生日,祝先锋,生日快乐!

让·彼埃尔·梅尔维尔曾说过这样的话,新浪潮没有特定的风格可言,如果说新浪潮确实有某种风格,那就是戈达尔的风格。
电影《精疲力尽》不仅是戈达尔个人漫长电影之路的第一步,也是整个电影史的一个支点。我不想说这是个丰碑或者里程碑,因为那终归只是意义上的冠冕。
戈达尔作品的出现却比“碑”更重要,他开光了这个卢米埃尔兄弟创出的新艺术形式,惠泽了众生,他创造的不是具体一个两个新的电影形式,他所做的也不仅仅是打破了一个两个具体的常规。他是一个支点,一点点小小的“打破”,供之后万千电影工作者们撬起地球。


“全世界的新电影中至少有一半是戈达尔的电影,也就是说它们遵循、效法着由戈达尔提出的标准和法则。”
戈达尔说:“电影是每秒24格的真理”。电影是由无数个“美”的瞬间组成,每个瞬间的真理“跳接”在一起成了一部电影,无碍约定成俗的元素与规则,心随意动指哪打哪。“一般来讲,电影要有开头、过程和结尾,但实际上,有时并不需要按照这个顺序”。
一切的瞬间都隶属于时间,每部电影中所谓的“开头”和“结局”,都是散漫在时间中的几个点,它根本无需规则可言,不值得除了出于戏剧性的考虑而在意。但说到底,戏剧隶属于戏剧性,戏剧性本身就是无迹可寻难以捉摸的,戈达尔的打破,是开拓。他不是定义了新的定义,而是革除“定义”,赋予“无限”。

其实新浪潮运动中,有很多杰出的导演拍出了很多杰出的作品,但我之所以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说新浪潮就是戈达尔的一枝独秀,是因为我把新浪潮,更多的不是看成一场运动,而且一种精神,具体点就是艺术精神,再具体点就是电影精神。
他在《电影史3-新浪潮》说道:“这是一个手太多,而心太少的时代。是的,一个缺心的时代可不缺工作,当一个时代生病了,没有工作给所有的手时,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新的挑战。一波新浪潮,不用我们的手,取而代之用我们的心去工作的挑战。我还不知道有哪个时代,缺乏工作提供给所有的心灵。”

要说戈达尔的过往,成就。那么戈达尔的过往就是“新浪潮”的过往,他附带着“新浪潮精神”衣食住行直至刚87岁的今日。他的成就,就是成就了新浪潮。在戈达尔诸多访谈和言论中随处可现其对资产阶级的抨击,然而他本身即出自资产阶级家庭。
1930年12月3日,让·吕克·戈达尔出生自巴黎,是家中第二个孩子,父亲是医生,母亲是当时著名银行家的女儿,他的童年时常住在他外祖父母的豪宅中,其资产环境足够明确了他出生的资产阶级属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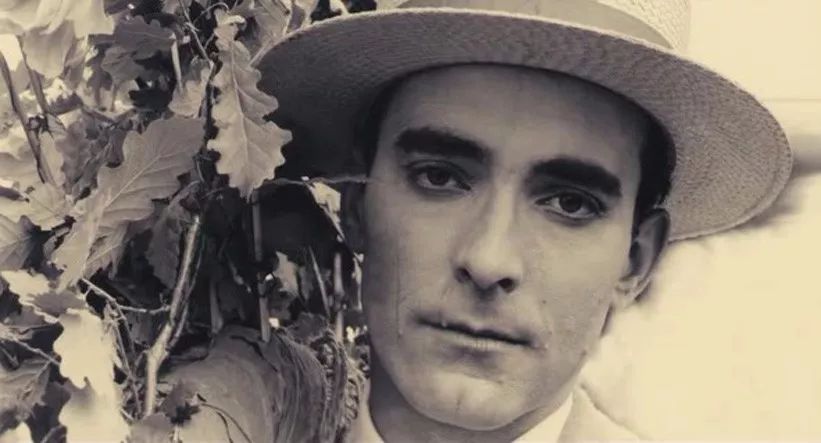
“我从资产阶级家庭逃脱出来,投身娱乐业,结果发现娱乐业也是个资产阶级大家庭,远比我的家族要大。而逃离这个娱乐业大家庭比逃离父母身边更困难”。
从对自己出身的资产阶级属性逃离,到斗争与抗击自己已经身陷的更资产阶级娱乐业大家庭,戈达尔的路注定是复杂的,他个人也注定是复杂的,甚至碎片化的,我们观望戈达尔导演,似乎只能通过各种不同形状的洞眼观望,再拼凑对他的认识。

在1948-1952年,戈达尔进入索邦大学并开始对电影产生浓厚兴趣,结识了一众后来在电影界声名鹊起的大导演,比如弗朗索瓦·特吕弗、埃里克·侯麦等人,并且共同组成了新浪潮小组,他们讨论电影、发表意见、提出主张,推动改革了法国电影,终究用种种“新浪潮行动”奠定“新浪潮现象”,并很快对全世界产生影响。

1950年,戈达尔开始在他与埃里克·侯麦、雅客·李维特创办的刊物《电影公报》上发表影评,后又于1952年首次在安德烈·巴赞编辑的《电影手册》上发表影评文章,并陆续在一些短片中出演角色。
直到1959年他拍出了第一部故事片《精疲力尽》,以离经叛道的电影语言和不可捉摸的戏剧走向,拍出了特有时空背景下超出时空的虚无,以散漫的故事结构和不成型的故事框架,拍出了新的戏剧表现形式,其剪辑和摄影丝毫不顾及观众的观影习惯,甚至刻意追求超出观影习惯的拍摄方法。

据说在拍《精疲力尽》时,他曾问过眼睛可以适应摇镜头的最大角度是多少,别人说是一百八十度,他马上告诉摄影师拉乌·库塔尔使用更大的角度。
“但人们去看你的电影是为了看电影”。
戈达尔:“我想要改变这一点,我不希望人们用看其他电影的方式来看我的电影,这一点需要改变,这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你的意思是你想要改变观众?”
戈达尔:“我在试图改变世界。”
1967年戈达尔在拍完《中国姑娘》之后,思想更加激进,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之后更是与当时的学生运动领袖结识并成立“维尔托夫小组”,狂热激进,用“实际行动”表达他们的政治思想,不仅“政治化”的拍摄出了一系列“政治电影”,还用摄影机之外的举动掀起他们自己的狂潮。

他凌乱芜杂的艺术风格,偏激执拗的政治主张,以及“他本人”。这一切使“新浪潮”就成了戈达尔,无论他如何极端鲜明甚至干瘪的一味宣扬他那被“大多数”孤立的言论、思想、立场,甚至采用各种看似“夸张”的方式去推崇,也不影响让·吕克·戈达尔与先锋画上等号。
毕竟,世界从来都不缺乏集体潮流,却始终奇缺个人色彩。色彩无美丑之分,色彩只存在有无之分,所以当我们在讨论戈达尔所偏激的内容时,更重要的是他的偏激属性带来的艺术奇观。

“娱乐新闻中那个面色苍白的戈达尔导演,总是伴随着打人、神经衰弱、企图自杀、绯闻和羞辱、安娜·卡里娜(第一任妻子)、安妮·亚泽姆斯基(第二任妻子)、旧的友情的破裂和新的追随者的出现,还有一直以来关于戈达尔终于彻底精神崩溃的传闻”。这是出自安德鲁·塞瑞斯的《戈达尔与革命》书中的一段话。
而不管他究竟是何人,最终那个真正的戈达尔,总是躲在黑色墨镜后面,脸上挂着一抹似有若无的礼貌的微笑,显出善意无害的,甚至是毕恭毕敬的风度。

说到戈达尔飞扬跋扈又深沉内敛的复杂性,戈达尔充满着人应具有的情绪化以及人类特有的丰富性格,他是个放大了的情绪动物,是个控制欲极强、多愁善感、难以交往、夸夸其谈、自视甚高刚愎自用的天才,他带着这些不易于处世的性格“把摄影机当作钢笔”书写他与既定世界的斗争。
这斗争必然是充满着挫败与苦痛的,但正如戈达尔所说,他“热爱工作,追求爱情”。即便曾长达十年一直挣扎在衰落和危机边缘,他非凡的精力和复原能力,旺盛的生命力和源源不断的思考性,依然使他颤巍巍又威风凛凛的斗争着行走着爱慕着憎恶着。

他曾指名道姓的批评了21位当时的重要导演,指出“他们的镜头运动如此笨拙,影片主题十分拙劣,演员表演呆板,对话缺乏意义,总之,他们不知道如何创作电影,因为他们甚至不知道电影是什么”。
并且随时表达他对好莱坞的鄙视——“不管给我多少钱我都不会为好莱坞工作的。我认为应当规定好莱坞只能拍摄16毫米和8毫米的电影,而地下电影则应当用70毫米来拍摄”。
直接表示对朋友的失望——“我的很多朋友,比如波兰斯基、让·雷诺阿、弗里茨·朗、德米等人,都到好莱坞来拍片了,我觉得这真是个悲剧,在我看来好莱坞的水准已经滑到了历史最低点。那些我曾经崇拜的好莱坞大师,如希区柯克、霍克斯、比利·怀德等,已经不再重视自己的作品了。他们的电影都已经落伍了。”

戈达尔1959年的第一部故事片《精疲力尽》就是在特吕弗的帮助下完成的,而后1959-1968的“新浪潮十年”是戈达尔与特吕弗相互帮助关系最好的时候。
但特吕弗回忆:“即使在新浪潮时期,友谊对戈达尔来说也只是一个意义。他非常聪明而且很会装蒜,大家都原谅他的心胸狭隘,但所有人都能证明他那不可掩饰的小心眼儿在那时就有了。你总需要帮助他,给他提供服务并等待回报,而他的回报,即是嘲讽与攻击。”
七十年代后,戈达尔开始对特吕弗持续的攻击,公开声称:“我觉得特吕弗绝对不懂拍电影,他只拍了一部真正与他有关的影片,就是《四百击》”。之后,戈达尔在电影之路上更加激进,而特吕弗却逐渐“温和”。

他的朋友总是亲昵的称他是“不讲道理的家伙”,他自己总是坚定的宣称“我几乎没什么朋友”,他忧郁深沉,其实在待人处事中又充满敏锐的感受力。
表面上不为所动漫不经心,内在波涛暗涌满腹激情,他对一切嗤之以鼻的态度来自于他的在意与好奇。就像他说“在我看来左翼人士都很感性很情绪化,而右翼则有些很铁石心肠,我是个多愁善感的人,所以我支持左翼,当然这只是原因之一。”
戈达尔导演的第一部英文电影,也是备受争议的一部电影《一加一》,由于导演和制片人对影片艺术内容相执不下,使世界电影史上首次将同一部电影的两个不同的版本,即——导演剪辑版和制作人版同期上映。
在伦敦国家剧院,该作制片人伊恩·卡里耶正在台上当着一大群观众的面介绍这部影片,戈达尔上前一拳挥上制片人的鼻子,并怀揣用来支付剧院费用的支票跳上舞台号召观众们要求退票。他因为观众只能看到这部电影的“制片人版”而十分愤怒,并补充,把退回的钱捐给埃尔德里奇·克利弗基金会。“那些拒绝捐款的人,都是资产阶级法西斯。”

戈达尔创作《精疲力尽》,以先锋打头阵,先锋了过去的电影史,又在后续不停的创作中一次次先锋了他自己。“帕特丽西亚”这个人物在《精疲力尽》中仿佛只留给了我们一个背影,于是戈达尔就认定《随心所欲》是从一个姑娘的背影讲起。
虽然最后还是从一个姑娘的侧影拍起,以一个姑娘一半的脸和间断的音乐开始,在开场这姑娘一半的脸中,我见到了一整部的《精疲力尽》,她不动声色的舔舔嘴唇,咽咽喉咙,空洞眼神,不就是那精疲力尽里暴躁无法掌控的虚无吗?

影片《随心所欲》一部有十二个场景的电影,一个出卖肉体灵魂纯洁的姑娘,在十二个场景中操持了一场茫然生命。游走于形同虚设的车水马龙巴黎街头,游走于可有可无的各种角色魑魅魍魉。

她四闯门房夺钥匙的一幕,带着无目的的虚空和有目的的冲动,电影视角始终平和却戏剧感强烈,这是本能的戏剧,是对生活亦步亦趋的摆脱和渐行渐远的深陷。
想到《精疲力尽》和《随心所欲》结尾,那宿命感的宏大和个体的渺小之死,不平凡的是这“新浪潮”电影,可又平凡的正如我们明日如今日一般的无尽生活。

从《随心所欲》开始,戈达尔感到自己已逐渐开始转为创作更具体的电影。1963年由法国尤物碧姬·芭铎出演的《轻蔑》,就是他创作生涯里为数不多较为具体的电影之一。影片《轻蔑》改编自阿尔贝托·莫拉维亚的小说《正午的幽灵》,或许从不写剧本的戈达尔用一个小说作为电影的发展根据,也是他之所以将它拍的较为具体的原因之一。
戈达尔总结《轻蔑》——“是一部形式简单内容深奥的电影”。该片采用了纪实电影的风格,以两条主线开展情节,一是碧姬·芭铎饰演的卡米尔对其丈夫情感上的渐生轻蔑,一是电影中的拍电影情节。两条线交错平行,共同进展,互相暗喻,其中还夹杂着戈达尔对待电影以及电影行业的种种看法。

另一方面,这部电影的用色也很值得玩味,高达使用“红”、“白”、“蓝”带动和象征欲望与情绪,红色欲望,再转为白色为正常摄影色泽,继而用蓝色来浇灭红色欲望。使用红白蓝,在1961年的《女人就是女人》以及1965年的《狂人皮埃罗》中都有体现。
除了运用色彩,戈达尔在一些电影里也突出“语言”的运用,比如:《我略知她一二》、《男性,女性》等,并多次在访谈中强调对“语言”的重视,批评好莱坞只把目光聚焦在眼花缭乱的画面上而漠视了语言的重要性。

在影片《我略知她一二》里,女主角几乎始终在“语言”着,哲学、生活、社会、政治……面对着摄像头,仿佛在直接与观影者对话以突出语言,也“刻意”证明了语言作为一种表达工具的有力,来对抗那些实利主义对观众兜售的低级诱惑。

“语言的产生显然就是为了跨越边界。对我来说,语言是我的祖国,而电影就是我的领土。”
在《高达论高达》这本书中,戈达尔将自己的电影创作生涯,区分成了“笔记年代(50-59年)”、“卡丽娜年代(60-67年)”、“毛派年代(68-74年)”、“录影年代(75-80年)”、“八零年代(80-89年)”和“电影史时期(89-98年)”。
戈达尔自“笔记年代”起就以影迷身份活动于电影场合了,此身份时至今日从未变过。在他80年到89年的“电影史时期”更是爆炸式表白电影,站在一个历经自50年至98年对电影的研究、评论、创作的过来人身份,重新诚挚谦卑的表达他深情的“电影之爱”。

从一个影迷到一个蜚声国际的大导演,反叛之后、斗争之后、困惑之后,还是顶着一头白发充满归属感的敲着打字机,喃喃自语声和打字机声错杂谈。
在胶片中、书籍中、影像中、声音中抚摩电影,念叨电影,剪辑电影,于是,就诞生了89-98年期间制作的这套《电影史(1-4)》。功成名就之后,有几个导演像戈达尔这般回过头几乎是饱含着爱情的凝视剪辑“电影”制作“电影史”!
曾有人对戈达尔说——您本人也是一个传奇。
戈达尔——我的传奇就是:一个不断与传奇抗争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