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桑塔格最后一部短篇小说集是出版于1977年的《我,及其他》(I, etcetera)。如今,一本名为《任务简报》(Debriefing)的全新短篇小说集即将面世,收录了《我,及其他》中的八部短篇小说以及另外三部:《朝圣》(Pilgrimage)、《写信现场》(The Letter Scene)和她最受推崇的、发表于1986年的作品《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The Way We Live Now)。相较于那些非虚构作品,桑塔格的小说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前者在文化领域有着极大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桑塔格的形象在去世后变得愈发高大,甚至有掩盖其作品光芒的危险:她以自恋狂、拳击手、卡米拉·帕格利亚的死对头及天才的形象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这部新短篇小说集严格来讲并未给读者带来什么新东西,但它确实让我们得以一窥桑塔格的另一面,而这一面常常被她另外两项更大更重要的影响力掩盖。
尽管桑塔格从来不会一直固守某种观点(《纽约客》杂志在为其所作的悼文中特别指出:“正如她所做的,她有权提出大胆的意见,并随着世界的变化而改变这些看法”),她把美国二十世纪的思想定义为“福柯式”或“麦克卢汉式”思想。《关于坎普的札记》(1964)、《反对阐释》(1966)和《论摄影》(1977)都是文学批评领域赞誉颇多的知名著作。桑塔格的作品涉及政治、疾病和大众传媒,并且写作一流。

[美]苏珊·桑塔格 著 黄灿然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年1月
这不禁让人回想起在《论摄影》中,她关于为何工业化强国(德国、日本和美国)会催生出一批批度假时拍照的游客的叙述:“使用相机能够缓解一种焦虑情绪,即这群平时忙于工作的人在度假放松时因觉得自己无所事事而感到的焦虑。他们要找些事情来做,让他们看起来就像在工作一样:拍照。”这便是桑塔格身上闪光品质的一个细微呈现:权威、出人意料又诙谐幽默。她并不对此横加批判,只是表现得像一个儿科医生,而我们如同被她量体温的小孩子一样。
帕格利亚最有名的两句挖苦之语描述了反桑塔格主义本质上的矛盾。桑塔格就是“一种肤浅的、故作姿态的代名词”,帕格利亚写道,但同时她也是“保守的文学世界道貌岸然的道德卫士”。要把这两项表述连起来解读并非易事,但如果我们把它们强行放到一起,在某些程度上来说也能讲得通:帕格利亚在桑塔格的身上看到了无尽的肤浅,新奇怪诞的旧时代气息混着乐于说教的潮流气质。就是这么个人,让作家凯西·阿克(Kathy Acker)都忍不住打趣一把:“亲爱的苏珊·桑塔格,能否赏脸读读我的书并帮我出名?”
桑塔格的短篇小说便是对这种刻板印象的一则有力反驳。并非所有作品都超凡脱俗,但它们各有特色。《中国旅行计划》(Project for a Trip to China)是一部有关中国的寓言式说教小说集,而讲述者从未去过这个地方,作品里更多的是关于这个地方的想象,而非描述一个真实的存在。通过这部作品,我们可以对这位有着东方情结的学者进行一番仔细考察,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中国的玛娜洛伊,中国的图兰朵。来自卫斯理学院的、美丽的有钱人宋氏三姐妹和她们的丈夫们。一个满是翡翠、柚木家具、竹子和狗肉的地方。”

在这篇小说中,桑塔格写作的形式让读者有机会了解由不同部分组成的散乱情结,这种情节甚至从句子层面上都算不上连贯。“我对智慧很感兴趣,也很热衷于墙壁,而中国正是以这两者闻名天下。”她详尽地描绘了这种从未经验证的情结。这让小说的形式变得更为有趣,其内涵却充满瑕疵,难免让人失望。这篇小说就是一堆馊主意的完美大杂烩。
在《朝圣》中,第一人称叙事者(很有可能就是桑塔格自己)回忆了青春期时不情愿地与托马斯·曼见面的场景。她最好的朋友梅里尔在电话号码簿上发现了他,并得到了星期天一起喝下午茶的邀请。讲述者对这种场合感到十分尴尬,这让她最喜欢的旧世界作家突然一下撞进了她枯燥无味的加利福尼亚生活中。她赴约了——“……我记得,他的小胡子(我不认识任何蓄须的人)看起来就像嘴巴上的一顶小帽子”——但每一刻都让她无比讨厌。
这是一篇怪异的小故事,结构不像小说,反而更像一篇个人随笔。除非我们把叙述者当成苏珊·桑塔格自己,否则这篇小说其实没什么意义。但《宝贝》(Baby)这篇小说要好得多,描述了一对父母与类似一名家庭心理医生之间的对话,但有些杂乱无章。在故事里,他们口中描述的孩子一下跳到7岁,忽然又到了20多岁,然后又成了一个婴儿或一个10岁的孩子。就像《中国旅行计划》一样, 《宝贝》的影响力也来自其形式。这是一个尝试,生硬但总体而言还是成功的。从这篇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桑格塔并未完全掌握这种叙事方式。
相比之下,《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则是形式和内容更完美的结合。这部小说讲的是一名患有艾滋病的男子——更具体地说,它的内容是病重的主人公和朋友们之间的谈话。桑塔格并没有描写这位患病男子,而是用电话交流的方式加以呈现。他们在电话中讲了些闲话,关于哪个人知道些什么、对有人站在道德高地批判的隐隐担忧,以及想要成为最被需要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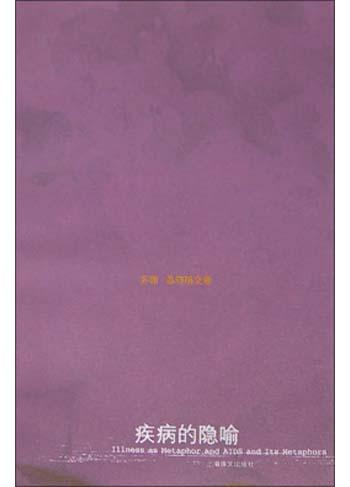
[美]苏珊·桑塔格 著 程巍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年12月
在她著名的言论“白人文明就像癌症”和《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及《艾滋病及其隐喻》(AIDS and its Metaphors)这两本书中,桑塔格对身体和语言之间的关系深感忧虑。她写道:“现代人对于疾病的心理探究尤为偏爱。”这正来源于心理学的科学氛围。心理学是“确保‘精神’高于现实的一种世俗方法,表面看起来很科学”,它会让我们将癌症看作是“邪恶无比的掠夺者,而不仅仅是一种疾病”。
《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更是把这种分析延伸到了我们讲话的方式上——把患有艾滋的生活故事当做由患病者的社区及其自身共同演绎出来的一种经历,为读者展现出来。在一个长句里,桑塔格向我们展示了疾病和语言之间永不停息的相互作用:
这确实令人振奋。斯蒂芬坚持认为,从一开始,或者说至少从他经人劝说最终给医生打电话开始,他愿意说出这个疾病的名字,并且说起来轻而易举,就像提到男孩、画廊、香烟、金钱或协议等寻常词语一样,但是保罗突然打断了他,因为斯蒂芬滔滔不绝地说着的这个词语是死亡的象征,每个人都必须接受这样一种象征,难逃一死、脆弱不堪、无一幸免,这种象征代表着人们愿意为自己的生命而战。
艾滋是这句话的核心,语言和患病的身体在此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这一疾病同时笼罩在错综复杂的狂热社区关系中,其中全是些在喜爱患者本人和代表患者讲话之间摇摆不定的说话者。
《中国旅行计划》的失败之处,在《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中取得了成功,后者展现了桑塔格写小说的天赋。两篇小说在形式上都颇具创新性,从她精心安排的比喻上来看,甚至有点过于追求形式化了。《任务简报》的写作也绝对可以称得上精妙绝伦。各个故事的品质千差万别,桑塔格审慎诘问小说主人公的情结和恐惧,让这些故事变得充满活力,也使得其中的好坏差别显而易见。《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检验故事形式的方式,与生活在备受折磨的社会中情感丰富的人们联系了起来。从初心到最终的想法,中间跨越了一个关键的节点:“不管是男孩、画廊还是金钱或协议,其实都没什么大不了。”
读完桑塔格的短篇小说,我们能了解这位著名知识分子的什么呢?在《任务简报》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自信且非常了解自己的作家,在遭遇失败时不停地进行尝试、提升自己。这本短篇集中有些故事根本不值得一读,但它们还是被收录其中,因为“苏珊·桑塔格”——作家离世后的人物形象强大到能够支持这种做法。但是正如阅读桑塔格不同类型的作品一样,你应该期待的,是其中的价值,而非其连贯性。
(翻译:熊小平)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