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区分作家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可以用他们擅长的文体加以区分;比如可以用世代进行分隔;但还可以有一种区分方式,促成了我们接下来要涉猎的这样一群作家——
中国当代的作家基本有两种存在形态,一种是“专业的”,他们加入各级作家协会享有某种身份和工资福利待遇。还有一种,则是体制之外的作家们,他们一个个更像是“单打独斗”的个体,没有组织,也没有体制。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大都还有一个别的身份和一份养活自己工作,甚至是养活自己的写作。他们很多人的文学创作要在晚上或者周末的时间里进行,他们生活得样貌千姿百态,若论共同点,大概只有一直持续、默默地写作着这件事。 我们就暂且称他们为“野生作家”。
其实,无论中外,全职以写作为生都是不容易的,很多人们耳熟能详的大作家也都并非全职写作:美国诗人T.S.艾略特是银行的评估员,卡夫卡是公务员,捷克作家赫拉巴尔年过半百时才专职写作,此前他做过列车调度员、废纸收购员和舞台布景工,而他们的“兼职”写作身份完全无损于作品的伟大。
回到中国,当代的“野生”作家们的写作形态是怎样的?他们对自己的写作和环境有着怎么样的期待和认知?他们的写作圈子又是怎样的?他们是否期待全职写作?我们将目光投向这些“野生”、自在生长出来的作家,就是想以他们的生存和写作姿态还原出中国文坛的另类的、多元的又充满生机的景象。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野生”作家史杰鹏的故事。
在北师大教书的时候,史杰鹏开过一门音韵学课程,音韵学很有趣,也很难,二十多年前,史杰鹏报考北大古文字专业研究生时,音韵学差点就成了他的拦路虎。

在课上,他好几次被好奇心旺盛的学生追问:“如果学好音韵学,比如把《广韵》整个背下来,穿越回古代能不能和古人对话。”
史杰鹏告诉学生,这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如今网络上流行的上古拟音系统,被录制成了音频材料,也绝非古人谈话时的真实发音:“他们如何说话,除非有录音,否则今天的人无法精确复原。”
答案让学生大失所望,史杰鹏脑海里却突然闪现出一个被音韵学串起来的模糊故事:一个古代的楚国大巫,机关算尽利用巫术与歌谣走了一步通向遥远时代的大棋,最后却功亏一篑,因为他没料到语言读音在未来的变迁。
日复一日,这个念头在史杰鹏头脑里挥之不去。太迷人了,他想,人是可悲的东西,对很多事情其实无能为力,这种无力却又散发出充满遗憾的美感。他决心要为这一缕灵感写出一部小说。
一、童年:农村不是诗人笔下的田园牧歌
据老同学回忆,学生时代的史杰鹏能整段整段地背诵《汉书》,很有点名士气象,对此,史杰鹏本人反倒谦虚起来,表示记忆已不真切,并毫不避讳透露自己儿时生活惨淡,父母也不幸福,几乎可以和穷困潦倒划等号。
提起在南昌郊外的童年,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其实我小时候的生活,和汉代下层人民的日常,并没有太大不同。”如果非要说出不同,那就是古人生活更为凄苦。
“你看《史记》里,讲到某某纵横家,路上被强盗抢走了一口锅。人们读到这里会觉得很好笑,但细想一下,背后是秦汉时代人出远门的艰难:不仅要自己挑粮食,还得自带炊具。商店、旅馆想都不要想,即使有也不是普通人消费得起的。”
一年吃不上十顿肉,使用牛与犁耕田,幼年的史杰鹏往来自己在南昌郊区的亲戚家,会瞧见悬挂在房梁上的竹篮,里面装的是上一顿没吃完的食物——挂在房梁上,老鼠就不容易偷吃。在没有冰箱的年代,中国南方农村家庭的储餐习惯大多不外如是。直到成年后回忆起这类细节时,史杰鹏才琢磨出这种储存方式必然为食物带来大量亚硝酸盐,从前的人,恐怕多少都已为此付出了健康的代价。
对一个出生在1971年的知识分子而言,这样的童年生活绝谈不上愉快。在史杰鹏的眼里,农村不是诗人笔下的田园牧歌,而是赤裸裸展示丛林法则的地方,他甚至体会不到太多亲情的美好。只有一点他是自小就看透了的:“猥琐是生活最真实的一面。”
在大学,史杰鹏见到了更多来自全省不同地方的学生,他惊奇地观察到许多乡村出身的同学都有类似特质,甚至连艰难生活带来的烙印都很相似:“易怒,为了一点点小事就会觉得自尊心受辱。”多年以后,当他投入在一系列汉代题材的小说创作时,乡村经验和伴随农村户口一道长大的敏感心灵,反倒成了他发挥想象力时的重要倚靠。
2003年,史杰鹏通过互联网发表了长篇小说处女作,长篇历史小说《亭长小武》,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个汉代豫章郡小吏借势爬上高位却最终走向悲剧的故事,前半段宛如侦探小说,后半段则加入了历史典故中的政治阴谋。为了方便叙事,史杰鹏把故事的发生地设定在自己的家乡。
“写一个在南昌发生的故事,我纯粹是寻找一种温馨的感觉,尤其是写到环境方面更加真切一点。”
《亭长小武》至今仍是他最畅销的作品,十几年来反复加印,史杰鹏自嘲后来在结构技巧上的探索很少受到读者认可,反倒是“小武”这类种马小说,脍炙人口,一版再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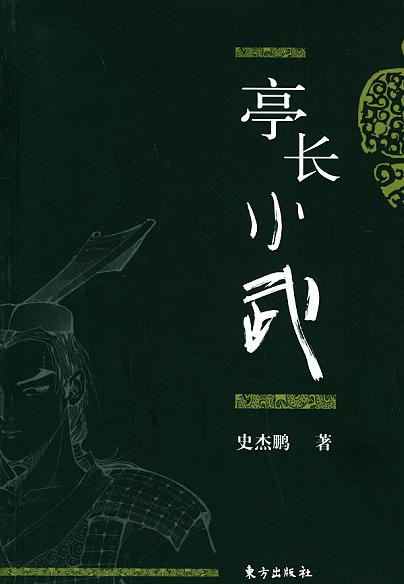
东方出版中心 2006-01
我被“种马小说”的提法逗乐了,史杰鹏却一本正经说,小武的故事是符合实际的:“汉代存在这样的社会现象,当时的人要改变命运,一部分会选择熟读律令,成为一名小酷吏。汉代不少丞相、御史大夫,就是从乡干部、派出所所长一步步做起来的,小武正是这样一个人。但做酷吏需要机遇,没有这种机会,就只能靠不顾一切的闯劲和钻营了,所以我后来写了和小武很不一样的《赌徒陈汤》。”
中央与地方豪强对立严重的武帝时代,一度是史杰鹏反复描摹的对象。他为之创作了《亭长小武》、《婴齐传》,稍后的《赌徒陈汤》尽管发生在宣帝年间,故事文本却与武帝时代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史杰鹏对帝王将相的故事兴趣不大,他更希望观察一个小人物,了解他们在那样的时代是怎么去改变命运。
这篇小说诞生后,一位学生告诉史杰鹏,自己看完感到非常失望:“这样一个人渣,怎么能当历史小说主角呢?”史杰鹏没有多做解释,在他心里,历史上真实的陈汤说不定人格更糟糕,自己的小说已经有拔高他的可能了。
“常有人说我小说里有种冷酷的世界观,其实那是我读《汉书》的感受。所以我说千万不要穿越到汉代,否则你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可能一个和你有点关系的亲戚被牵连了,你也得莫名其妙陪着被杀。你知道汉代腰斩是要先把犯人衣服剥光的……”
史杰鹏会忍不住描述其中的细节,仿佛赵忠祥解说动物世界,听者偶尔意识到这些都是两千年前真实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残酷往事,不自觉便毛骨悚然。

民众热衷追忆古代的帝王伟业,对充当背景布的普通人的际遇缺乏兴趣。史杰鹏感到滑稽:“我认为,历来老百姓崇拜的英雄人物,大多是残害百姓的人渣。”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史杰鹏刚刚完成创作的新小说《刺杀孙策》,这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反英雄小说。“我的历史观和很多人不一样,孙氏家族在江东,巧取豪夺,非常残暴,以不讲信用著称。基本是个没什么文化的家族。”史杰鹏想通过这部小说来阐述他对三国人物的看法。
为了创作《刺杀孙策》,史杰鹏从湖南走马楼出土的吴国简牍中提取了不少基础信息,涉及孙吴时代的统治方式、基层官吏的运转模式,虽然故事出于虚构,但史杰鹏自信在历史感上,会比当下流行的三国题材创作好很多。
历史感,一直是他的文字追求,缺乏历史感,则一切小说都只是作者对时代做出强硬设定的当代小说。史杰鹏明确表达过对人气小说《大秦帝国》的厌恶,表示看到“白雪“这种人名就不想看了,因为作者并无还原历史场景的能力;他也通过《故事新编》中“小穷奇”“小丙君”一类的人名,表示过对鲁迅古文功底的认可。
“我的理想,其实是写出一部完全不涉及上层斗争的历史小说,彻底的平民视角,一个古代版的《户口本》。但文献材料还支撑不起这个构想,也许过几年我会尝试一下。”
《户口本》是史杰鹏的自传体小说,描写他自江西农村长大过程的所闻所见,出版于2016年,很多读者说,这是他最好的作品,一部完全意义上的当代史和个人史。史杰鹏想,倘若能写出一个古代版的《户口本》,这大概就是历史小说的极致了吧。
二、求学:从菜农之子,成为大学者的传人
为了写小说,特地去释读出土的竹简,这听上去完全不是小说家应该做的事,但史杰鹏的写作与秦汉文献渊源颇深,在他的一部小说《亭长小武》诞生时,竹简就帮过他的大忙。那时,史杰鹏正在研读一批出土于湖北张家山的汉简,汉简中透露的某些信息让他兴致盎然。
“我这个人呢比较感性,张家山汉简对汉代人的生活细节披露非常详细,我看了就觉得那些人非常可怜。里面讲了一个刺杀的案子,特别生动,我把它照搬进了《亭长小武》,也就是小说第一章的故事。它是汉代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一开始,史杰鹏只打算就这个刑事案件卷宗写一个短篇小说,他将故事发表在自己和好友檀作文合办的BBS论坛“生于七十年代”上,架不住网友纷纷说好看,史杰鹏干脆顺着故事写下去,中途将连载阵地换到了天涯社区,点击率一路暴涨,最后竟虚构出了三十多万字。
“可能这种小说以前没有出现过,里面关于汉代律令的描写,要有专业背景。”小说出版后,中影也找上门来买下了影视改编权。2008年,中影再次找上史杰鹏,邀请他为吴宇森导演筹备的历史电影《赤壁》提供剧本创作,合作者是刘震云。
“我执笔,刘震云作为指导。写完第一版,刘震云觉得非常好,说就该这么写,但最后吴宇森没有采用,拍电影的时候用的还是自己的理念。”自己的创作最终没能被搬上荧幕,史杰鹏有些遗憾。但他也明白剧本与小说对于技巧的要求天然不同,对他而言,前者带来收入,后者则满足创作欲望。当然,还有古文字学,那是他的本业,也是吃饭家伙,同时也是他热爱的一门愿意以之为志业的学问。
对古文字的兴趣源于《红楼梦》,史杰鹏从小感性,高中时是完全意义上的文学青年,他热衷诗词,并对《红楼梦》中毒颇深。上大学后,在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图书馆里,史杰鹏翻遍了每一本解读《红楼梦》的作品。有天,他从一本编写于文革期间的汇编资料中读到了王国维的文章,以叔本华哲学思想分析《红楼梦》,史杰鹏顿时感到五体投地,他对这个原本仅被与《人间词话》联系在一起的前清遗老刮目相看,顺理成章地了解到了王国维的本业之一:小学。
古文字学,亦称小学。究其本意,指的是秦汉时代的字词句。这些文字的书写、读音在历史中逐渐变得面目全非,最终,原本真的是连小学生都知道的文字知识,变成了大学者才有能力解读的艰深学科。史杰鹏发觉自己进了一个全新领域,并且自己兴趣不减。
“对小学产生兴趣,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不希望自己看古文的时候要依靠别人的注释,因为注释总会出错。”
九十年代初的江西师大显然不是一个适合研究小学的地方,随着自学的深入,史杰鹏知道了裘锡圭、李学勤这些古文字大家的名字,并以他们的作品为纲,对古文字领域的教材进行系统性的阅读。
“裘锡圭有篇文章,叫《谈谈怎么学习古文字学》,我按照他的说法,看了郭沫若的《卜辞通纂》、《殷契粹编》,还有一些音韵学的著作。”读的书多了,史杰鹏冒出了追随这些大师进行学术训练的想法,他开始向裘锡圭写信,表达有意报考北大古文字专业的愿望,在信件的地址一栏,史杰鹏填上:北京大学中文系。

不久后,裘锡圭亲笔写的回信真的来了。信中,裘锡圭告诉这个对古文字深怀兴趣的江西青年,自己已经不带硕士研究生了,但北大的另一位学者李家浩,同样学识深厚,他或许愿意接纳新生。没过几天,李家浩的信也来了,他只是谨慎地对史杰鹏说,这年学校的确希望他招一位硕士,如果史杰鹏实在有兴趣,可以试试。
收到两位学界大拿的回信,给了史杰鹏极大的鼓舞,他几乎把全部的时间都花在在接下来的备考过程中。从结果看,史杰鹏的自学效果不错,他顺利通过了1994年的北大研究生入学考试,通往学术世界的大门被撬开了。
“考研的时候,有道音韵学问题我答错了,后来李家浩老师问我这事,我就很老实告诉他,书看了好几遍,确实没弄懂。因为音韵学真的很难。”史杰鹏继续作出解释,“古汉字本身并不是绝对指代特定意思,更像一种记音的语言,同音字之间可以通用。我们今天叫通假字,当时人其实不觉得,汉字对他们就是记音符号。所以如果不知道某个字当时的读音,就很难确定他指代的是今天的哪个词。不懂音韵学,研究古文字就瘸了一条腿。"
李家浩是战国简帛的专家,在九十年代中叶,中国出土的竹简规模还不大,可解读的文献有限,简单的信息早已被破译,没人做的课题大多很有难度。史杰鹏选择1987年出土的包山楚简作为研究对象,他把想法告诉裘锡圭,裘锡圭想了想,提醒他:“这个题目有点难哦。”
“要在他们手下过关,是很难的。但最后我拿出了七条札记,两万多字。”史杰鹏毫不掩饰自豪,无论是李家浩还是裘锡圭,对待学问和作品都极为严格。史杰鹏印象深刻的另一次收到褒奖,是在自己的散文随笔集《旧时天气旧时衣》出版后不久,接到李家浩的电话:“你里面有些文章,写得挺有意思,知识面也丰富。你知道我这人平时很少夸人。”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01
三年的硕士生活,给史杰鹏的未来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他从一个菜农之子,成为了大学者的传人。1997年,硕士毕业的史杰鹏打算找份工作,在北京扎下根。同一年,北师大创办了国学研究院,负责人听说李家浩今年有个待就业的学生,立刻向他发出了邀请。史杰鹏近水楼台先得月,顺利加入了北京师范大学,他在这所学校完成博士阶段的研究,导师是王宁。
“王宁先生的老师是陆宗达,陆宗达师承章太炎、黄季刚,所以我的博士导师是章黄学派传人,章黄都是我景仰的大师,虽然其严谨性不如清代的王念孙、段玉裁这批人。”说起小学,史杰鹏立刻与小说话题无缝切换,滔滔不绝,“王国维、郭沫若的学问虽然很好,但思维还不够严密,对文字的释读多数还是猜测。这也是自古的传统,比如郑玄在讲古文的时候,经常不顾语法,认为一个字可以在任何位置使用,所以他解释出来的东西很多是不可靠的。裘锡圭这派在老一辈上大大进了一步,引进了西方语言学的思维方式和语法观念。”
“很奇怪的是,这种想法在清代的王念孙身上产生过。王念孙在讲一个词的用法的时候,会引用很多遵循相同语法的例句。说明他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史杰鹏在北师大一待就是20年,白驹过隙,国学研究所早已换成了古籍所,史杰鹏也成了副教授。在这期间,他写写停停,从小说到剧本,到评论专栏,均有涉猎,直到在那节音韵课上和自己苦等多年的题材相遇。
但史杰鹏没能一挥而就,这个由音韵学串起来的楚国故事折磨了他整整三年。
三、写作:赤裸裸地展示生活的猥琐
“要承载这样一个故事,肯定得找到恰当的结构才能将作者理念表达出来,但就是一直找不到。”
史杰鹏不想重复自《亭长小武》以来的历史小说套路,早在写作《赌徒陈汤》时,他就已经在小说里加入新的技巧,尝试让不同的人物回忆同一个角色,以碎片式的段落拼接出完整故事。这次,他想在结构上再大胆一点。

东方出版社 2007-05
构思主线故事期间,史杰鹏仍在坚持读小说。一天,他胡乱翻开胡安·鲁尔福的名作《佩德罗·巴拉莫》,鲁尔福是马尔克斯的偶像,也是享誉世界的拉美文学代表人物。史杰鹏看到一半,忍不住一个激灵,心里梦寐以求的故事结构和讲述方式,瞬间豁然开朗了。
“《佩德罗·巴拉莫》对我有不小的启发,很散,婵变式的小说。我的写法是分了章节,他不分,读起来更绕。但他的时间线不是很长,我在《楚墓》里设定是几千年的故事。”
《楚墓》问世后,史杰鹏的读者群发生了严重分歧,一部分认为史杰鹏突破了过去历史小说的局限,文学性在他的个人写作中被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是小说中间插入的一篇训诂论文,以及结尾处节外生枝的一章,都被看做神来之笔。另一部分读者则完全不买账,他们抱怨《楚墓》的故事杂乱无章,颠三倒四,且逻辑上极不可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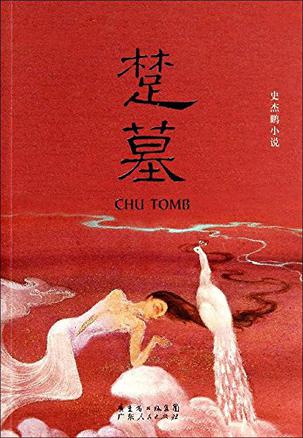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4-07
除了偶尔在网络上打打笔仗,史杰鹏没有过多纠缠于争论,他开始全身心投入下一本小说的创作,这是一部来自江西农村少年的个人史,史杰鹏早已为它想好了名字——《户口本》。
“户口本这个东西,在七十年代对中国人的影响之大,现在可能无法想象。如果你户口是农村的,基本就是二等人。所以它对我当时的心灵和后来性格也有影响,让我小的时候很羞涩、敏感、自卑。”史杰鹏在这部小说里倾注了自己自童年以来对于人性、家庭、乡村社会的观察和体认,据他描述,小说中的大部分故事都来自他的亲身经历,偶尔会加入同龄朋友们的回忆。
“我从一开始就想用一种比较别致的方法把过去的细节展现出来。写的时候受巴别尔《骑兵军》影响比较大,他对环境的描写让我很受用。还有查尔斯·布考斯基,他对小说人物卑微猥琐的形象描写,《户口本》里的人物大多都这样。”
但史杰鹏真正感受到了对这篇小说拥有把控力,是在看完了库切的《青春》和奈保尔的《米格尔街》之后。“我当时想了很多种方法,绞尽脑汁,最后采取每章构成一个独立小短篇的方式来展示我的整个生活环境,写到一半,看了奈保尔的《米格尔街》,感觉就像遇到了知音。算是和大师不谋而合吧。库切影响到我的,是他对自身挖掘的力度,他连从前诱奸自己表妹的事情都写出来了,我想这一定是真的,西方人自我剖析的力度确实很有冲击感。不看他的小说,我肯定不会像这样挖掘自己,看完他,我就觉得,应该这样写作。”
《户口本》的出版为史杰鹏带来了道德困境,他在小说中将身为“铁公鸡”的父亲和菜农母亲卑微的形象展示得一览无余,同样的待遇也被施加到每一个史杰鹏想得起来的亲友身上。早在散文集《旧时天气旧时衣》中,史杰鹏曾写作过不少关于过去记忆的描写,但那时笔调依然饱含温情,在小说《户口本》里,史杰鹏选择赤裸裸地去展示生活的猥琐。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6-11
一个身在南昌的堂姐读完《户口本》后非常气愤,通过微信痛骂了史杰鹏三次,然后再和不和这位堂弟说话。“她怪我把自己写得猥琐就算了,还把他爸妈也写这么猥琐。但实际上,在我眼里,他们都是这么猥琐,但他们不愿意承认。因为农村就是很猥琐很卑微的生活方式嘛。我大伯伯家的女儿也看了书,她也说有很多地方不舒服,但他们能理解我,而且有些段落回忆小时候的生活细节,他们会来告诉我,说写得满生动的。”史杰鹏向自己的微博关注者们展示了自己和堂姐的微信截图,对被刻画者的主观感受,他走向了彻底的不关心。
《户口本》的故事只写到史杰鹏十八岁为止,对于此后的岁月,他说自己依然有提笔的欲望。史杰鹏在十八岁后就离开了从小生活的南昌城南郊区一带,并在4年后北上,在北京落地深根。
“如果继续写下去,就是我离开家乡以后的事情了,那么,我希望能写得更加不温情。”一想到这种可能,史杰鹏也忍不住笑起来。
四、去职:在北师大工作20年,离开只用了不到20天
2017年夏天,史杰鹏46岁了,他第一次尝试用安眠药改善自己的睡眠质量,在朋友家做客的时候,他看到了几盒三唑仑,顺便问朋友讨要了一盒。在那之前,他已经连续好几天睡不好觉了。
睡眠问题困扰了史杰鹏很多年,他自小神经衰弱,失眠时有发生。刚进北大读研的时候,史杰鹏的上铺住着古代文学专业的同学檀作文,檀作文床头摆着一个闹钟,每到深夜,滴答声不绝如缕,直沁耳膜。没几个月,史杰鹏濒临崩溃的边缘。他一言不发地从海淀市场买回一个没有滴答声的新闹钟,平静地向檀作文提出交换的要求。
后来,史杰鹏把这段往事当做笑料写在网上:“当时檀作文应该庆幸自己接受了交易,否则歹徒梁惠王拿回来的就不是闹钟,而是一副哑铃。”
“梁惠王”是史杰鹏更响亮的花名,那是在20世纪初,他和檀作文共同在诗词论坛上厮混,檀为自己取了网名“周穆王”,史杰鹏翻了翻《孟子》,顺手就选了梁惠王做自己的名字。“每次都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叫梁惠王,我就说觉得他这个人挺不错的,老被孟子骂,也不发作。”他停顿了下,然后挥挥手,说那些理由其实是扯淡,“就是随便选的,没有原因。”

几个月前,史杰鹏失去了他在北师大的教职(古籍所副教授,副高七级)——他在北师大这里工作了20年,但离开只花了不到20天。
现实摆在他眼前,他的工作,没了。
“完全就是耍流氓。”据他回忆,收到教务处的解聘通知的日子恰好发生在北师大放暑假的前一天。他认为,这么做无非是想让自己没有申辩的机会。解聘影响到的不仅是他个人,还有跟着他研究甲骨文的研究生们,“北师大搞我这个学问的老师没几个,我一走,好几个学生都得去改论文选题。”
史杰鹏的睡眠质量在此后剧烈恶化,甚至彻夜难眠,终于到了不得不求诸安眠药的地步。比起丢掉工作,这件事给自己家人带来的错愕更让史杰鹏难过,而且这也很可能让其他大学对他避之不及。史杰鹏有点后悔自己从前在社交网络上的口无遮拦了。
“别人都觉得我爱骂人,但实际上我是不适合这种交流方式,我2011年开始用微博,当时网上很热闹,说话很大胆,但我发现经常有不认识的人疯狂来骂你,不知道怎么回事,让我非常震惊,我一度不想上了,后来有朋友劝我说网上不就是这样嘛,习惯了也还蛮好玩的。所以我继续用了,我想我骂人的风格可能也是微博培养出来的。”
生活中里史杰鹏,远没有那般激烈。他的学生们耳闻了老师在社交网络上的形象,反倒觉得有点萌,私底下也开始叫他“大王”起来。
“我性格比较刚直,受不得委屈,现在想来,这样的性格往往会受更大的委屈,代价很大。”史杰鹏说,他最在意的是没有把现实身份和网络ID切割开来。
“我并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是史杰鹏。但当时开通账号的时候,我是受邀请用户,账号信息已经由工作人员注册好了,实名,还备注了我是北师大副教授。等我自己修改成历史小说作者后,已经有很多人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了,由不得我。
末了,他只好叹了口气,“中国人就是这样,因为你的一些说法,就去你的工作单位告状,给你穿小鞋。这样的结果,都是互相长期不宽容带来的恶果吧。”
短暂的沮丧过后,史杰鹏又回复了梁惠王的神情,现在他开始专心经营自己的微信公号“梁惠王的云梦之泽”,并尝试制作面向大众的古文字学线上课程。即使对于学术,史杰鹏仍未放弃相关研究工作。
“我最近两三年的论文都是关于秦汉简的,原先不是,我毕竟对包山竹简很熟悉,但因为我博士研究的是训诂学,在词源学方面下了很深功夫,所以后来一直在做词源学研究。现在秦汉简大量出土,我发现利用词源学研究可以解决秦汉简不少问题,这两年写了十多篇文章,但生性懒散,一直没有修改发表。”
“古文字研究的成果,没有专门的期刊供你发表,但你可以发各个大学的学报,原来古文字的文章必须手写,出现电脑照排之后可以剪切上去,就好办多了,但你知道,学术圈存在很多人情稿,我可以肯定地说,那些有刊号的期刊里,很多学术文章质量比不上本行当的集刊,但它们在考核上有便宜,因为有刊号。”
五、未来:创作一部以20世纪历史为蓝本的小说
在国学复兴的时代,史杰鹏无疑是个满脑子离经叛道思想的异类,他是古文字专家,却丝毫不认为需要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保留所谓的温情;面对甚嚣尘上的文化复兴热,他总是泼出一碗碗冷水,提醒跟风者不要脑子过热;身为学者出身的小说家,他对欧美小说的熟稔程度和对文学性的追求,在历史题材写作者中显得格外醒目。
他曾经完成过一篇《卫鞅》,看过人都说,那是他最好的中篇小说。他还说,自己最大的野心是创作一部以20世纪历史为蓝本的小说作品,他希望把故事背景放到战争时期,从人性和人权的角度出发,让现代价值观介入故事,更直白地展示冲突。
“你熟读《汉书》,又对汉代律令了如指掌,假如把你扔回汉代,你觉得自己能活下来吗?”听到这个问题,史杰鹏沉思片刻,声调降低下来,说:“估计活不了吧。”
他反问:“孔融、祢衡这些人,难道就不懂祸从口出的道理吗?其实就是性格使然,一时激愤,把命丢了。我知道很多道理,可我做不到。”
同题问答:
界面文化:你最欣赏的外国作家是谁?为什么?
史杰鹏:太多了,查尔斯·布考斯基,弗兰纳里·奥康纳,俄国作家有巴别尔,还有我特别喜欢的契科夫,还有普宁、海明威。我过去几本小说里,受过明显影响的还有库切、奈保尔。
界面文化:你最欣赏的华语作家是谁?为什么?
史杰鹏:我喜欢刘震云,以及苏童的一些短篇小说,他的长篇我不喜欢,形式上有点幼稚。现在已经好久不看国内作家作品了,看了也不喜欢。
界面文化:你的社交圈里是否有许多作家朋友,是否认为写作应该进入某个圈子?
史杰鹏:我没什么作家朋友,没有加入作协。我想如果有一个圈子的话,可以互相砥砺,但如果没法跟圈子里的人和谐相处,只能不加入了,因为性格使然。我在写一个小说后,会给我的朋友看看,我会给出版社,比如《楚墓》当时有的出版社看了就不想接,认为太文学了,他们建议我投文学类期刊,但我也不认识这方面什么人。
界面文化:除了写作和阅读,你还有什么爱好?
史杰鹏:我会打两盘游戏,那种射击游戏,一进去打两把就出来,其他没什么爱好,要做家务,照顾孩子啊,时间有限。
界面文化:你认为作家和评论家是否应该保持距离?
史杰鹏:我觉得应该吧。
界面文化:你写作的习惯是什么?是否会在固定的时间写作?
史杰鹏:会专门有个创作状态,每天写两千字左右,写完小说,我每次都想修改十几遍,但总是做不到,能修改三五遍就很可以了。
界面文化:如何看待影视和文学的关系?
史杰鹏:好久没看过电视了,家里的电视机都不打开了,有段时间我看过《大明王朝1566》,还不错,至少对生活细节有描绘,其他历史戏很少对生活细节有细致的描写的。我曾经做过一个剧本《西楚霸王》,刚开始对方很兴奋,但没过多久,电视台就要开播《楚汉风云》,陈道明演的。当时我交剧本的时候,对方提醒我,你要脸谱化一点。只要脸谱化才有辨识度。影视和文学的另一个差别是生活化的细节,在剧本里不需要多写,老百姓不看的,你只要写冲突就行了。
我会去读好剧本,有次我写过一个电影剧本,《天山之战》,写耿恭的,我就看了一些战争题材的剧本,《拯救大兵瑞恩》这些,想写好剧本还是得看好莱坞电影剧本才行。但还是很难完全把它和中国的故事嫁接起来。
界面文化:你觉得未来文学的读者会更多还是更少?
史杰鹏:我觉得纯文学的读者可能少了吧,看网文的人很多了。但网文我是真的看不下去,前些年有一部很火的爱情小说,里面有个角色“玉面小飞龙”的那部(应指《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我的妻子告诉我说她的朋友评价这部小说”太完美了”,我就在Kindle上下载了看,发现这什么玩意啊,太扯了,完全看不下去。
界面文化:我们谈论一部小说时,会说到语言、结构、节奏、故事等等,你最在意其中的哪个方面?
史杰鹏:结构,我个人的看法是结构更重要,一个故事如果找到一个很好的结构就可以非常完美地表达出来,我为了给《楚墓》寻找结构,等了三年。文字技巧当然也很重要,但那是第二位的。
界面文化:写作的时候你会想到读者吗?
史杰鹏:不是完全不考虑,我会想想读者会不会觉得是否合理,但如果我想表达我的价值观,就不管那么多了。
界面文化:作家是否应该关注政治话题,公共性话题?
史杰鹏:我认为应该关注,作家写到最后不是拼文学修养,而是拼思想境界,如果一个作家完全不关心政治,我不认为他的思想境界会高到哪里去。最终你还是得思考这些东西,关注这些话题不仅是应该,还是必须。
人物简介:史杰鹏,历史小说作家,古文字学博士,原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副教授,1971年出生于江西南昌,现居北京。师承著名古文字学家李家浩、王宁,对古文字学、训诂学、先秦两汉文献学有深入研究,曾参与多部影视剧本改编创作。出版文学作品:历史小说《亭长小武》《婴齐传》《赌徒陈汤》《楚墓》《刺杀孙策》,历史随笔《文景之治》《楚汉争霸》,散文集《旧时天气旧时衣》,自传体小说《户口本》等。网络常用名为“梁惠王”,现为独立撰稿人。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