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区分作家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可以用他们擅长的文体加以区分;比如可以用世代进行分隔;但还可以有一种区分方式,促成了我们接下来要涉猎的这样一群作家——
中国当代的作家基本有两种存在形态,一种是“专业的”,他们加入各级作家协会享有某种身份和工资福利待遇。还有一种,则是体制之外的作家们,他们一个个更像是“单打独斗”的个体,没有组织,也没有体制。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大都还有一个别的身份和一份养活自己工作,甚至是养活自己的写作。他们很多人的文学创作要在晚上或者周末的时间里进行,他们生活得样貌千姿百态,若论共同点,大概只有一直持续、默默地写作着这件事。 我们就暂且称他们为“野生作家”。
其实,无论中外,全职以写作为生都是不容易的,很多人们耳熟能详的大作家也都并非全职写作:美国诗人T.S.艾略特是银行的评估员,卡夫卡是公务员,捷克作家赫拉巴尔年过半百时才专职写作,此前他做过列车调度员、废纸收购员和舞台布景工,而他们的“兼职”写作身份完全无损于作品的伟大。
回到中国,当代的“野生”作家们的写作形态是怎样的?他们对自己的写作和环境有着怎么样的期待和认知?他们的写作圈子又是怎样的?他们是否期待全职写作?我们将目光投向这些“野生”、自在生长出来的作家,就是想以他们的生存和写作姿态还原出中国文坛的另类的、多元的又充满生机的景象。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野生”作家袁凌的故事。

初次见袁凌是在北京师范大学一场非虚构作家交流会上,几位国内比较知名的非虚构作者面对着台下新闻传播专业的学子,讲自己眼中“什么是非虚构”。袁凌上台发言,说“文学已死”,他认为当代文学几乎脱离了当下社会现实,成为空洞个人情感的抒发。他讲得很激动,话筒有点故障,被他震得嗡嗡响。

再见袁凌,是在北京东五环外的皮村,一个外来打工者聚集的城中村,他受邀为打工者组织的文学课授课。点评打工者的作品时,另两位老师更多是鼓励,袁凌却针对几处问题在探讨,显得有些执拗。下课后,袁凌找其中的两位月嫂留下了联系方式,月嫂显得蛮开心, “我们有好多故事,可以给你提供素材”。此时已是晚上十点,袁凌要从东五环奔向自己北五环的家。
袁凌住在北五环的昌平,我们的采访就约在他家附近,与之前两次见面的印象一样,他依然显得执拗又随性。作为一个深度调查记者,袁凌目睹过许多人间的荒诞和苦难,但这并没有给他添上一丝世故,他反而是朴素而天真的。他看起来不像是一个俯身于某个村庄采访调查,受到震撼然后匆匆离开的局外人,而就是从匮乏的山村里走出的一员,而他也的确如此。如今他生活在北京,但和市中心的繁华保持着距离。
“我们的命就是这么土”,就像袁凌的书的标题,他生辰八字里有六个“土”,父亲给他取名字的时候又不小心加上两个,“土”是袁凌的命运。“如果让我过得很逍遥很满足,我反而会感到很失落。”
九十九次死亡的筛齿
袁凌第一次看到死亡是小时候在一棵核桃树下,生产队上一个打核桃的年轻人从最高的核桃树梢摔下来,头朝下,没出什么血,几乎没发出一点声息就死了。他在《我的九十九次死亡》中写道:“像是草丛和玻璃窗上一滴水渍的去世”。
袁凌出生在陕西安康的一个村子里,安康位于陕西省最南端,与湖北、重庆交界,习俗和方言偏向于南方。袁凌出生的地方叫“筲箕凹”,“筲箕”是一个形象的比喻——一个扁竹筐。村庄四面环山,与外部沟通困难,北边是秦岭,南边是巴山,汉水流过,地下遍布煤矿。
在这样一个村子里,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出生的袁凌对童年最深的印象是饥饿。他两岁时,父亲读了工农兵大学,成为了那个年代少见的“高级知识分子”。可读书,就意味着家里少了一个劳动力。父亲上学的那四年,一家四口人的口粮,只能靠母亲和姐姐来挣,工分太少,袁凌经常吃不饱肚子。粮食吃完了,袁凌就和姊妹几个背着背篓,到生产队收获过的地里挖遗留下的土豆。小孩的饥饿也是普遍的,生产队掰玉米的时候,大人会故意在苞米杆上漏下几个玉米,孩子们就跟在后面哄抢。
在贫穷荒僻的村庄里,人的生命是微浅的。“一个乡下孩子活下来和长大的过程,也就是他身边的人不断死去的过程。这像是一种暗中的挑选。”身边的孩子出天花、被烧伤、落树、蛇咬、溺死、掉魂,都是挑选的手段。而成年人的死亡更多地来自煤矿。一次,队办煤矿出了事故,七个大人躺在炭洞门口的煤渣上,头枕着一堆坑木,袁凌觉得他们的耳朵像是坑木长出的木耳。
袁凌起先读的是村办小学,一二三年级一起上课,全校只有两个老师,校长的文化水平是小学五年级。三年级时,父亲将他转到了镇上的学校,留母亲和姐姐在家中。袁凌和父亲住在父亲工作的医院,但他更怀念村里的生活。父亲不会做饭洗衣,更不会表露温情,袁凌十分孤独。每到周末,他要不顾一切地走上十几里山路,回家见见母亲,星期天再下山回镇上。
医院也是充斥着病痛和死亡的地方。袁凌特别怕上厕所,计划生育运动里人工流产的婴儿尸体都会被倒进厕所,蹲在厕所时,袁凌觉得那些婴儿会伸手上来掏他的肠子。有时会送来车祸后的伤者,摆在院子里,袁凌在院子里走,就从那些正在死去的人身边穿过。

袁凌 著
广西师大出版社 2014-07
当袁凌开始写作,他出版的第一本书就叫作《我的九十九次死亡》,书里就是九十九个死亡故事,不止九十九条生命。袁凌认为自己是命运的筛眼中留下的孩子,他必须做一个记录者,“请身边所有人留下遗言,如果有人没有遗言,就记录下他们的沉默”。筛齿一定会在袁凌身上留下伤痕,就像他手臂上至今留着的一道惊心的烫伤疤。
走出出生地
袁凌考入了西安的大学,从秦岭南坡来到关中,“过秦岭”是一道门槛,跨过去就成了异乡人。长散文集《从出生地开始》写了袁凌如何第一次走出家乡,他坐着汽车,车顶上绑一个巨大的黑漆木箱,经过一整夜的车程来到西安。他报考的是中文系,带着自己的文学梦。
八十年代文学热的风已经吹到了袁凌生活的小镇上,光父亲工作的医院里,就有三个文学青年,他们订了《人民文学》《当代》《小说界》等杂志,初中的袁凌除了上课就是将自己泡在这些杂志里。所以那时袁凌写作文很好,他记得老师经常在课堂上念他的作文,还给他批语,“如银珠落盘声声悦耳”。高中流行起互赠明信片,在背面抄席慕容的诗,或是写两句自己的诗,袁凌也就开始写起了诗。
大学一年级,袁凌说他已经能写别人看起来很成熟的现代诗,但很快他对现代诗产生了怀疑。“我觉得现代诗是以意象和象征为立足点的,追求的是一种言外之意,但我是排斥这个的。在诗里面我需要看到的是真实经验的传达。”他开始摸索一种新的诗歌路子,抛弃晦涩、浑浊的部分,追求透明,然而起步是艰难的。大二时他的写作失了宠,他拿着写满诗歌的笔记本去找辅导员,他记得辅导员草草翻了几首,“显出极度的失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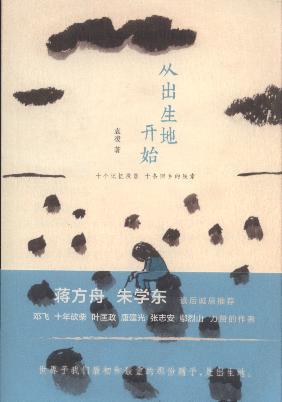
袁凌 著
法律出版社 2014-11
袁凌觉得文学应该接触更多的现实,而不应该在象牙塔,大学毕业,他选择了回到家乡的县城。他在一家法院做书记员,也跟着去跑案子。他进入案发现场,去看守所提犯人,与关押的犯人聊天。“法院对生活的参与是实质性的参与,一个官司一个判决可以改变他们的生活,那是在记者的角色之下体会不到的真实,是内部性的材料。”但受不了法院里有些人的排挤,袁凌待了几个月就离开了。他去市里当了两年大专老师,觉得无聊,又考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
研究生毕业后袁凌就进入了媒体这行,他不想留在上海。“上海是一个过度成熟的商业社会,它没有文学,文学就是用来表现人类生存的矛盾处境的。而且我从小是生活在冲突性中的,我不习惯悠然成熟的生活方式。”《重庆晚报》来学校招聘,袁凌问:“你们那里是不是有很多农村?”“是的。”于是袁凌就去了重庆。
来到《重庆晚报》,袁凌先是做校对,然后上街扫街跑新闻,之后又被调到经济部、国际部,做的都是豆腐块的小新闻,反倒因为上夜班累出了一场大病。生病带来了机遇,袁凌被调到了周末部,开始做起了深度调查。他做了一些大型的采访,例如三峡蓄水、丰都城搬迁、重庆开辟新水源的调查,还拿过重庆市新闻一等奖。
不过采访中袁凌更珍视的是来自个体的小故事。他采访过一个被强暴的幼女,女孩八岁,被清理垃圾的工人收养。袁凌见到她的时候,女孩正坐在棚屋里一辆板车上,肚子和双腿都肿了,已经不能走路。袁凌蹲下来问她:“你想不想活?”那女孩吃惊地抬起眼睛,对袁凌说:“我想活。”两天后,女孩死在了棚屋里。这个故事后来被写进了《我的九十九次死亡》。
在工作期间,袁凌一边写新闻,一边进行着自己的文学摸索。他努力在二者之间筑起一道高高的防火墙,让两边互不侵犯。
他的摸索是“野路子”,既不像小说,也不像散文。“我觉得我要写我能够感受到的真实的经验,而不是去讲好故事,因为你要坚持自己,你必须排斥故事,这样会产生大量的不成熟的、自我强迫的东西。”和写诗的经历一样,读研究生时袁凌曾在很多省级刊物上发表过作品,但当他开始寻找自己的风格,并且认为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风格的时候,却没有人愿意发表。袁凌被无数次的退稿,它们不遵守任何规范,无法归类。那对于袁凌是一段漫长的黑暗期。

写给家乡簌簌的土
在重庆待了四年,袁凌想要离开,本想去《南方周末》工作,但遭到拒绝,他转而考了博士。2003年,袁凌进了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拜入葛兆光门下。同一年,《新京报》创刊,他去应聘,通过了面试。
袁凌在《新京报》的第一篇特稿作品是《北京SARS后患者骨坏死调查》,这也是《新京报》第一篇深度报道。然后他开始一边马不停蹄地出差、采访、写稿,一边在清华上学,“累得头发都掉了”。清华大学的课程跟袁凌设想的不太一样,他感兴趣的是现代思想史,但导师的研究方向是古代思想史,学生们要从考据做起。袁凌感觉“师兄弟们一个个像虫子一样钻在故纸堆里面”。坚持了半年,袁凌提交了退学申请,导师没有过多挽留,批了一句:“与其多一个不情愿的学者,不如多一个有良心的记者”。
这一次,袁凌在媒体的行业做得很顺利,他从《新京报》到《财经》,又到了新浪,从普通记者做到了管理层。做记者表面上满足了袁凌对接触现实生活的渴望,但他心里隐约感到不安。“人家生活好久,你去写一个稿子就走了,好像很生动,能叫生动吗?人家生活了一辈子,你写了五天,能叫深度报道吗?”他觉得自己亏欠了生活的真正经验。
2005年春节回家,袁凌看到大河转弯的坡岸上建起了一排小楼房,代替了从前的土屋,而小溪边有人家修了直排厕所,粪便不经处理地排进河里。梯级水电站大坝截流,上下游的河道干涸风化,里面是烂掉发臭的死鱼。“以前乡土也在消失,但它是一种慢性的渐变,到了90年代后期,因为市场经济的加速,它忽然变成了断裂。”断裂的危机感抓住了袁凌,他想赶着记录下行将消失的乡土。
袁凌辞去了在北京的工作,再次回到了乡下。老家的房子早就卖掉了,袁凌先是和一位算命的亲戚住在废弃的粮管所里,后来又在前妻家开的小商店里待了一年。商店开在路边,有几条小路通向四面的山上,山上的村民每十天半月背一个大背篓下山,买一背篓日常用品回去。还有来自四面八方的行人在这里歇脚。
小时候热闹的乡村,如今变得空空荡荡,路上很少遇到年轻人,剩下的都是些老人。一次一个老人进店里讨水喝,老人有两个儿子,说好一家住三个月,在一家还没住满就被赶了出去,另一家也不要他。他在路上来回走,走不动了,就进来要杯水。半天后,袁凌听说那位老人走到下面水潭边,跳河死了。
“整个农村是分崩离析的,不仅是经济、是自然、生活习惯。”但袁凌要做的不是进行价值判断,也不是抒发乡愁。“我能做的并不是大喊大叫,不是痛哭流涕,而是把那种曾经存在过的生活形态记录下来,以后它们完全消失了,别人看到的时候觉得,曾经的人还可以这样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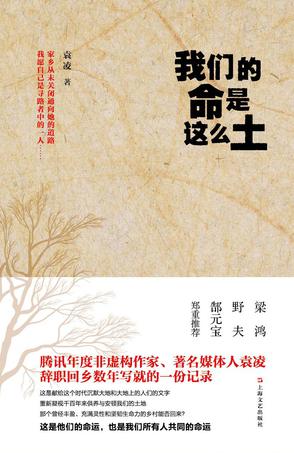
袁凌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6-01
袁凌用一年多的时间里写下了一系列小说,一部分收入了小说集《我们的命是这么土》。真正命土的是那些一辈子在土地里劳作的农民,他们的生活单调、乏味。袁凌写的小说也不太像小说,它们十分散淡,写农民静静地劳作,静静地留守,慢悠悠地走来走去,或者静静地死去。袁凌用大量的细节置换了情节,用经验置换了故事。
“我想,一篇小说如果没有着力去写土,写出那种簌簌的松散又凝聚的质地,那也就没有真的去写农民。”
青苔是卑微,然而不死的
从家里面出来,世界已经变了,袁凌又从一名普通记者开始入行,辗转了几家杂志。这时“非虚构”的概念开始逐渐被公众接受,从何伟的《寻路中国》,到梁鸿的《中国在梁庄》,非虚构作品在图书市场热销,新闻界也开始使用文学化的叙述方式。袁凌以前写的“四不像”的东西,突然都可以装进“非虚构”这样一个篮子里了。
2012年袁凌开始写特稿,原来新闻和文学壁垒分明的界限被打破,他在其中找到某种平衡。他相继写出了《守夜人高华》《走出马三家》等一系列影响颇广的稿件。在网易开创的非虚构栏目“真话”上,刊登了袁凌的一系列作品,然后出版社也找了过来。袁凌积压的大量作品一本接一本地出版,包括非虚构故事集《我的九十九次死亡》、长散文集《从出生地开始》、小说集《我们的命是这么土》,还有特稿作品集《青苔不会消失》。
《青苔不会消失》中的故事一个个让人沉重得喘不过来气。地点有埋满了战争遗留下来的地雷的村庄、被矿难和尘肺病夺去无数年轻人生命的村庄、有毒的砷矿腐蚀了土地和全村人健康的村庄,还有打工者混居的北京城中村大杂院,留守老人和儿童守着破败屋瓦的大凉山……而在那里生活的,是十七岁被地雷截断双腿的农妇,双膝跪在沉重的铁皮板凳上,收割比她还高的麦穗;在矿难中失去双眼的老人,依靠摸索重建了自己的整个生活;下生受创干枯的年轻人,在土屋里的床铺上,二十年如一日地穿针绣鞋垫,供养自身和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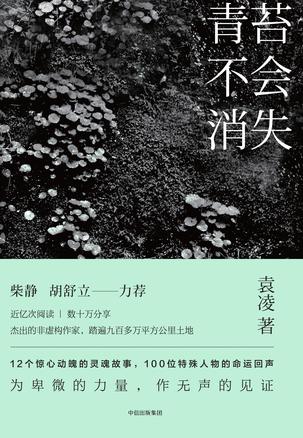
袁凌 著
中信出版集团·中信大方 2017-04
如何承受生命里目睹如此多的苦难?对袁凌来说,他从小早就习惯了这种状态,他把它们看作是一种生活常态,那不是悲惨,而是生活的一部分。那些像青苔一样卑微地活着的人,他们内心是安宁的。“青苔是有价值的,它有生命,不是死的东西,那种没有生命力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东西,还比不上一个不那么干净但是有生命力的东西。”
也有责难的声音,为什么面对这么多的社会不公,袁凌不去试图改变什么,而仅仅在书写?“恰恰是一个面向现实的作家才面临这样的谴责。”但袁凌知道自己的职责。“我是一个写作者,不是一个社会活动家。”这并不意味着袁凌是一个文学至上的人。 “其实到后来你觉得文学都不重要。文学性对我来说没什么意义,我不喜欢把一个什么写的漂亮。重要的是我希望能够把我们存在过的经验保留下来。”
如果在记录的同时能做点什么,袁凌说他也去做了。最近两年他参加了一个乡村儿童探访的公益项目,到全国各地的乡村儿童家,每次生活半个月,写下他们的生活状态。过程极端艰苦,偏远山村缺水缺食物,有时没有床,要睡在木板或草堆上。在新疆,他要翻雪山、走八九个小时的山路。到后来,袁凌经常头晕,在一个村子里给老人测血压时,袁凌也上去测了一下,老人的血压是140,袁凌的血压竟然有180。
在袁凌心中,很多文学作品是“干干净净的尸体”,而袁凌只有在一种状态下能写东西,就是建立在可靠经验的基础上,让它像一棵树在土地上生长起来。“文学到现在一定是一种实践活动,不再是一种想象活动,你的生活方式和你的文学一定是合一的,你对别人经验的表述,和你自己的生活形态不能是彼此矛盾的。”袁凌曾经为没能一直生活在乡村而愧疚,但现在他想通了些:“那时候我在《新京报》已经是管理层了,我没有选择继续做下去,我过的是现在这种生活。我并没有一边在作品里去写苦难的人,赞美一些卑微的生命,自己遛着狗住着豪宅,做着高消费。”
也许推动着袁凌写作的核心,是他从出生地背负而来的一种“负疚感”。“从一个乡村出来,你会觉得那个地方是你的负担,因为那地方很贫穷,它被人损害,你忘不掉这个地方。”就像沈从文曾经说过,一个人心里面有七八十个故事压着没有写出来,他的日子怎么过?对袁凌来说,写作是一种偿还。“没有把这些东西写出来之前它就是欠的,把这些东西写出来,你才算是不欠了。”
- 同题问答 -
界面文化:你最欣赏的外国作家是谁?
袁凌:我内心喜欢的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我觉得他写了一个有点软弱的知识分子,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有点软弱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都是有点软弱的,你会敏感,会想到很多事情,会有比较丰富的感触,再加上我们还写诗。《日瓦格医生》这部小说里面包含了很多东西,有诗性、知识分子那种东西,也有大时代的东西。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有点高不可攀,因为他非常的坚硬,你会崇敬他,会受到他的影响,但你觉得他真的有点太可畏了。在英文里面就喜欢哈代,因为哈代也是很诗性的,他也写乡土,他的语言我比较喜欢。
诗人最喜欢保罗·策兰,还有荷尔德林。策兰的诗跟我那个时候诗的追求其实是暗通的,它抛弃了现代诗的晦涩、讲究象征意象,策兰的诗你以为不好懂,其实很好懂,它保存下来的就是那种无可置疑的人类的生存经验,他的每一个字都是非常可靠的,他具有一种坚实的石头一样的质地,而这是其他的现代诗人不可比的。他是一个在奥斯维辛之后有权利写诗的人是吧。荷尔德林是由于他有把信仰和诗性结合起来的能力,因为我这个人对信仰也是有兴趣的。
界面文化:你最喜欢的中国作家是谁?
袁凌:现代作家我最喜欢的是孙犁,我喜欢他的语言,孙犁的语言是登峰造极的,没有人可以比。他在一个革命年代里本身也是革命阵营的一员,但是他的语言超脱了意识形态,超脱了现代语言的晦涩,他的素朴性非常的强,而字的表现力是自然而然的。孙犁是汪曾祺的老师,但是汪曾祺的语言就有刻意的味道,包括沈从文也是那样。但是孙犁不是,孙犁就是他觉得因为这个事情要求他这么写,他就这么写,他写出来之后那种沈静、节制、素朴,我觉得你要是把他外表的什么解放区作家抛掉,看他内核的东西,他真的是一位语言上的唯一的大师吧,现代文学里面没有人可以跟他比的,鲁迅的语言也是很刻意的,我不喜欢语言的刻意,我喜欢素朴。

界面文化:你写作的习惯是什么?是否会在固定的时间写作?
袁凌:我写作时间大体是固定的,一般是早晚,晚上不会太晚,就是12点以前,早晨也不是太早,就是八点多,下午有时候写的,就是要看状态好坏,状态不太好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会慢慢酝酿一下。不一定每天都写,但是基本上还是一个相对正常的写作状态,如果不出差的话。
界面文化:除了写作和阅读,你还有什么爱好?
袁凌:我用来休息头脑的一般是下围棋,有时候看点电影,其实我是一个乡土长大的人,如果你给我一个合适的环境,我还是蛮多爱好的,比如游泳、爬山,但在城里面呆着的话,也无非就是一天固定地散个步,然后就是下围棋。
界面文化:你的社交圈中是否有很多作家朋友,或者是否认为写作应该进入某个圈子?
袁凌:这是个矛盾的问题,完全不认识人,你就会很难很难。我上研究生的时候,其实有机会去接触一些一线的作家,放弃了,觉得过早地接触不是什么好事,自己也没什么作品,那些年写作的黑暗期,也不认识什么作家,投个稿都挺难的。现在因为毕竟出了一些书,发表一些东西,就慢慢地会认识一些作家。不太想为了这个事去社交,就像何伟说的一句话,你把时间花在社交上,还不如去接触你不熟悉的人。我也不是什么体制内的人,也不参加作协组织的活动,跟一个作家,你们俩聊什么也挺无聊的,说实话,很多情况下你也没怎么看过他的书,他也没什么看过你的书,就是看了又怎么样呢,除非非常必要的见面,见面还是不多的。
所谓的的圈子我就更觉得更没意思了,与其有宁可没有,它有好处,有可能可以得到一些奖,得到一些承认,但是现在也想开了,首先我不是过不下去,我也能发表东西,至于说是出版还是在哪个杂志发,是在顶级杂志发还是不那么顶级的杂志发,在这个自媒体时代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也不在乎要活得很好,或者说也不像年轻时候那样,一定要有“宇宙一样的名声”,那何必呢,再加上混圈子混出来名声能有什么意思呢,也是很腐朽的。
界面文化:你如何看待影视和文学的关系?
袁凌:某种程度上小说改编成电影,我还是可以接受的,因为电影也是一个讲究长度的东西,长度有限,里面会有某种节制的东西、紧凑的东西,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我可以接受我的东西被改编成一个电影,甚至可以接受自己来改编成一个电影剧本。但是我接受不了电视剧,电视剧太可怕了,明明只有那么一个几十分钟的情节,你非要拿到几十集,我觉得一个作家如果开始写电视剧,那他已经死了,因为他的语言注定会变成拖拖拉拉,无病呻吟的。
界面文化:谈论一部小说会说到语言、结构、节奏、故事等等,对你来说,你最在意哪个要素?
袁凌:我觉得一个小说的要素可能还不能这么分,我都不喜欢“小说”这个词,现在这个词被用得过度,实际上我们最好说是一部文本。如果说以“叙事”和“文本”的概念来说,它最重要的就是质地可靠的人类经验,在这种经验的前提下容纳了你说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为了要更好地表达这个经验,也可以说这些东西就是经验的一部分,比如我们的语言本身也是我们生存经验的一部分。但现在对我个人来说可能难题是在结构上,这是一个技术问题,就像一个楼房,都是真材实料,你还要学着把它盖得合理些,我想我会做这方面的努力,但是你说什么最重要,我想肯定就是里面传达的人类经验这样一个质料,这是最重要的。
界面文化:写作的时候,你会想着读者吗?
袁凌:那没工夫去想。是这样的,你写第一遍的时候应该不会想,但如果一个东西长期地改,后来你会想到这个问题,是不是我把它写的更有益读者阅读一些。我现在这个长篇小说,就在想这个事情,那也只是说是找到一个对话、交流,而不是说我就是奔着读者去写,那样其实读者也不会买账的。尤其是不会因为一个时代的整体口味去写,可能我对话的读者是我的一种潜在读者,而不是摆在那里的读者,要轻阅读软阅读的那些读者,我肯定是没办法跟他们对话的。
界面文化:作家是否要关注政治和公共性话题,并有义务将这些反映到作品里?
袁凌:这个问题挺矛盾的。我们这些人由于是媒体圈的,很容易跟公共生活发生直接的联系,我觉得找不到一个万全的办法,如果说你忘记了本份,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政治活动家,你肯定就完蛋了,但是你的写作在什么程度上触及到公共议题,我觉得还是要触及,只是说触及的时候能不能把它消化掉。当然我们会受到这种诱惑,一个大时代里,尤其是我们想到现代文学史的时候,茅盾、巴金这些人迎头就扑到政治里面去了,过了很多年以后他们的作品都站不住,反倒是像沈从文、张爱玲、萧红这样离得远远的,反而站住了。到底我们是趟这个浑水好呢还是干脆别趟它好呢,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处境,当你就在这个里面的时候,你也没有什么办法,去做鸵鸟也没有用,所以我在想,至少不能把自己当成一个活动家吧。
我一直也在积累一些素材想反映比较广阔一点的、综合一点的社会经历,但是这样做的时候总是摆脱不了内心的痛苦,因为这个东西毕竟比起你成长的经历,比起一些微小的生活,没有那么熟悉,你会不会用了很多的劲之后完全搞砸,会不会发现你下的那个功夫还不如不费?因为我写一些东西都是从我真实的经验出发的,当这一部分的经验还没有那么透的时候,我就会比较困惑。所以我想这个也没有办法,不是说我们完全不涉及公共问题,而是只有在我们的经验足够的时候,能够很自然地把它表达出来才去写它,而不是说我们有一点概念,我们有一个立场,觉得我要站个队,看起来可能很正确,但有什么意义呢?它留不下来,我想也只能是这么一个长期积累的态度。
界面文化:你觉得未来文学作品的读者会更多还是更少?
袁凌:文学从来都不缺读者,只是看是什么样的文学了。有时候我们也没必要把这个问题看得太严重了,你想《甄嬛传》,它算是纯文学还是不纯呢,在有些人看来,它大量地借鉴了《红楼梦》的手法,你能在其中看到它对传统的继承,它里面用的古字是很雅训的,比很多现代作家对古典文学的继承要也好得多。我们一般作家没这个本事的,这帮供在文坛上的大佬作家没这个功底的,他们不怎么读书,脑子里就是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故事,把小说严重矮化了。所以说到底什么样才算纯文学,到底文坛外的高还是文坛内的高,不一定重要。从这个前提来说,如果我们不那么计较文学和非文学的界限,不那么计较高雅和通俗,我觉得文学的读者它始终有,只是说这些不同的形态之间需要对话,也需要对抗,我们也能从papi酱身上找到营养,网络语言里面也有好的东西,只是说你要跟它有张力。不是说几个传统文学圈的人就可以把持语言,那种语言往往也很腐朽。我觉得这个问题没那么重要,读者会始终有,你只要不是固步自封,不是守着几个经典不放,莎士比亚当时也是个戏子,只是后来被捧成经典,我觉得都没什么要紧,文学的读者始终会存在的。
界面文化:你是否认为作家和评论家应该保持距离?
袁凌:评论家我也不认识几个。如果说你受到他的影响,按评论家给你布置的去写,肯定是不太好,如果你跟他交往的时候就作为一个朋友,一个交流,我想也还是可以的,尤其是当这个评论家自己也写作。如果有一个人,他认识到了你作品的好的地方在哪里,我想是很有安慰的,这个东西有时候读者给不了你,同行也给不了你,一个评论家,他就是搞理论的嘛,他能够认识到这个东西,就还可以。但如果一个普通读者能够到这种深度,你得到的安慰也是一样的。一个专业的人有些时候可能更没有见地,他看东西太多了,就麻木掉了。我想就随缘吧,认识的就认识,不认识也没关系,没有必要专门去结交,我也没有专门结交过什么评论家。
界面文化:你在写作这条道路上对自己未来的期许?
袁凌:我想如果有期许的话,外部的期许也没什么意义,也就是自己能够在一种安心的状态里面,一方面能接触到实际的生活,另一方面慢慢的去感受,能够最终完成一个比较困难的任务,不至于变成内心很空虚,生活的压力没有大到让你崩溃这样一个状态,能够有规律地写作,这样持续写下去。
以后我能具体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写出什么样的东西,可能能看到近期的,但看不到远期的,远期的东西想多了也没意义,四五十岁这年纪也不小,就觉得能写点东西就写点东西。另一方面来说人肯定会有一两个东西是强迫自己的,对自己来说有点困难的,这东西有,我也不愿意多说,因为也不知道将来能不能写出来,会试着去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但是不是最终还是很失败,现在都说不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