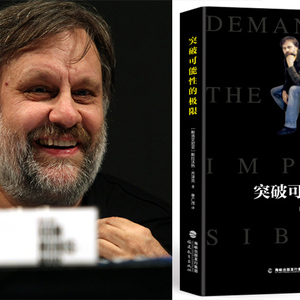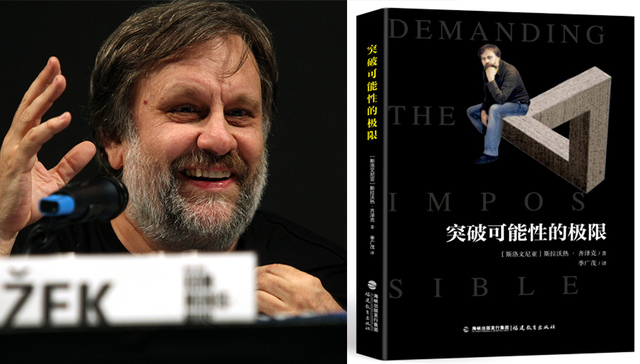如果你可以与哲学家、文化理论家斯拉沃热·齐泽克畅谈未来,你会问出什么问题并得到何种答复呢?
2009年5月,齐泽克曾在《新左翼评论》上发表文章《如何推倒一切,重新来过》,他引用了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最后一部散文小说《向西去啊》(Worstward Ho)中最后一句话:“再尝试,再失败,更好地失败。”齐泽克试图以此表明,列宁当时有一个主张:不仅要放慢脚步,巩固已经取得的成绩,而且要重新回到起点,推倒一切,重新开始。用著名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话说,革命的过程不是循序渐进的过程,而是重来复去的过程。
那么,推到一切究竟是推倒什么?重新开始又要开始哪些?如果说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度的联姻已名存实亡,那么我们该如何如何设想一个新的未来?为全球资本主义寻找一个怎样的替代方案?新型的美好社会是何种形态?如果我们不选择“推到一切、重新开始”,什么样的未来在等待我们?如果说是一种新威权主义,那么它危险在哪,又与旧威权主义有何区别呢?在《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一文中,齐泽克带着读者向未来窥视了一眼。
这篇文章收录于《突破可能性的极限》(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5月版)一书中,作者齐泽克在书中敏锐观察着当下最新的世界变局,从金融危机、中东动荡等入手,对当今欧洲民主制度与资本主义面临的困境做了前沿的分析,试图不断探索新的出路,对无产阶级、私有公共空间等传统理念进行了拓展,对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世界范围内的生态问题、政治局势等展开了全新解读。齐泽克在最后提出,“我们必须拆掉何者可能与何者不可能之间的界限,并以新的方式重新界定这条界线”,即我们不能受“可能性”的约束,要突破可能性的极限,方才有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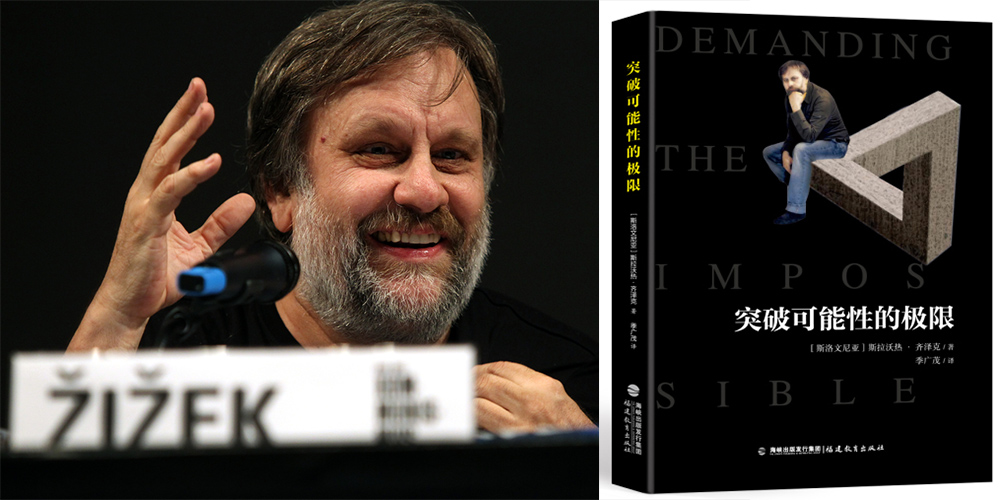
《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读者希望从你的共产主义概念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但他们可能已经感到失望。我也相信,世俗左翼的义务不仅在于为意识形态而战,而且在于推倒一切,重新开始。你曾经引用列宁有关贝克特式最佳结局的谈话。正如你在引用列宁的话时所言,推倒一切,重新开始,会带来巨大的问题。你曾经提到,实际上,如今资本主义无法迈过的难关是,我们无法设想一个切实可行的替代性选择,以替代全球资本主义。我们真的无法预想一个替代全球资本主义的替代性选择?何者会成为我们唯一可能的选项?你如何描述新型的美好社会?关于未来,你是怎么想的?你渴望得到怎样的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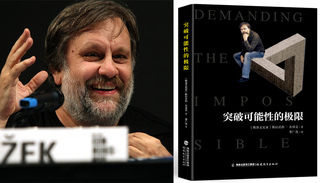
齐泽克:如果你问我,我们的未来会如何,那么,我设想的社会样式是这样的:你是否看过特瑞·吉列姆特瑞·吉列姆(Terry Gilliam,1940~ ),出生于美国的英国剧作家、电影导演、动画设计师和演员,迄今为止执导过12部故事片。1968年放弃美国国籍,加入英国国籍。执导的精彩影片《巴西》《巴西》(Brazil),又译《妙想天开》、《异想天开》,上映于1985年。本片内容跟巴西毫无关系,它讲的是有关未来英国的故事。未来的英国是官僚独裁之地,管道遍地,办事繁琐,官僚作风严重。因为一个意外的错误,一个无辜者被捕并被害。主角是政府大机器中的一个小螺丝钉,碰巧发现了这个错误,由于良心发现,尽力纠正错误,结果越陷越深,最终无法自拔……?
它上映于近乎30年前,但那是一部出色的影片,一部疯狂到家的喜剧,展示了未来英国的面貌。未来的英国虽然由极权主义政权统治,却不乏隐秘的享乐主义快感。当然,快感不是庄严肃穆的威权式的(authoritarian),而是大权在握的格劳乔·马克斯(美国著名喜剧电影演员,马克斯三兄弟之一)式的。意大利前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迈出的第一步,岂不接近于此?而且,在某些国家,在私人生活层面,没人关心你私下里获得的变态快感,只要别招惹政治,即告万事大吉。它不再是典型的法西斯主义动员。
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正在穷尽其局限,我们需要采取步调一致的大型社会行动。否则,我们未来必将类似于电影《巴西》中的情形。我觉得,在规训秩序(disciplined order)的范围内,新威权主义将不同于旧威权主义,但它将导致怪异社会(strange society)的出现。在这样的怪异社会中,在消费主义和私人生活的层面上,你将获得全部的性自由,获得你想获得的一切。与此同时,你将拥有某种非政治化的秩序(depoliticized order)。这个想法很可怕。那么,我们应该对此做出怎样的评价?在共同感(译注:common sense,一般译为“常识”。为了强调“共同”二字,这里译作“共同感”)、共同方式(译注:common manner,一般译作“常见礼仪”。为了强调“共同”二字,这里译作“共同方式”)的语境下,共有物的另一个意义至关重要。这是我为什么喜欢令人震惊,告诉他们说,我支持威权价值观念(authoritarian values)的原因。
支持威权价值观念,我这样说,是什么意思?不妨举例说明之。我不愿意生活在这样的国家中,在那里,你不得不与人争辩,强奸妇女是不对的。这很淫荡。连这样的价值观念都需要大肆争辩,这是怎样的社会?我愿意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在那里,毫无疑问,强奸绝对被视为令人恶心和发疯的事情。这道理同样适用于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对某个社会的伦理状态的权衡,不依赖于某些被人争辩的事情,而依赖于某些被视为不成文的规定而被全然接受的事情。比如,在欧洲,你看不到“不许随地吐痰”、“不要丢弃食物”之类的标语。我并非在高高在上地蔑视他人,我只是听说,在个别国家,真有这样的标语。但是在欧洲,人们不经思索就能理解。你根本不需要把它写到墙上。我觉得,这就是社会的伦理标准。这标准不是明确禁止或允许的东西,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被接受而又毋须提及的东西。如果你看欧洲,不难发现,标准正在急剧降低。
从这个意义上说,二三十年前被视为无法接受的事情,如今越来越多地得到了认可。比如,二三十年前,让极端右翼执掌政权,这个想法是不可接受的。极端右翼已被“革出教门”。所有小型的新法西斯主义政党,如奥地利的约尔格·海德尔(奥地利政客,一直秉持极右政治立场,支持德国纳粹),法国的让-玛丽·勒庞(法国极右党派国民阵线领导人),莫不如此。我们不搭理他们。我们身处民主社会,所以我们宽容他们。但要让他们执掌政权,那绝无可能。但这原则已经轰然倒塌。你现在在奥地利和别的什么地方,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突然成了值得尊敬的人。我们是这样看待法西斯主义的:到目前为止,在欧洲达成的共识是,法西斯主义是个坏东西。但是现在,你必须为此展开论争。而且,如同我断言的那样,和法西斯主义一样,种族主义也会越来越多地引起论争。甚至在埃及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我觉得,西方会越来越多地被迫放弃民主制度,即使我们必须坚守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这样说会变得越来越时髦:“是的,民主制度。但你不能直接实施民主制度,有些人还没有成熟到那个地步。”以色列已在公开这样说:“我们支持穆巴拉克,因为埃及人还不够成熟,无法在那里实施民主制度。”但这岂不具有讽刺意味?因为这次革命本身证明,埃及人渴望民主制度。我真的觉得,我们正在迈入具有潜在危险的混乱时代。我认认真真看到的,是不同于法西斯主义的新威权社会。我不喜欢许多人宣称:“啊!这是新法西斯主义!”我不喜欢“法西斯主义”这个术语,因为我要表达某种新东西。我甚至不喜欢他们以隐喻的方式使用该术语。他们以隐喻的方式使用该术语时就像在说某种精密之物,但他们全部的所作所为都暴露出,他们缺乏分析。
有人把如今发生在匈牙利的事情描述为法西斯主义。他们在这样做时,不过是在说:“我不喜欢眼前发生的事情,它们只是令我想起六七十年前发生过的事情。”这可不好。我觉得,世界如今正在寻求真正的替代性选择。你愿意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上吗?在那里,你要么选择盎格鲁-撒克逊新自由主义,要么选择亚洲新加坡式的具有亚洲价值观念的资本主义。令我提心吊胆的是,借助于这种具有亚洲价值观念的资本主义,我们会得到远比我们的西方资本主义高效和活跃的资本主义。但我并不认同我的自由派朋友怀抱的希望。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度的联姻已经寿终正寝。华尔街给我提供的教益是,有了真正的乌托邦,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拥有不同的社会。真正的乌托邦只是事物实际的样子,实际事物会无限期地、一如既往地延续下去。我敢断定,我们就要做出某些艰难的决定。如果无所事事,那我们显然会进入新的威权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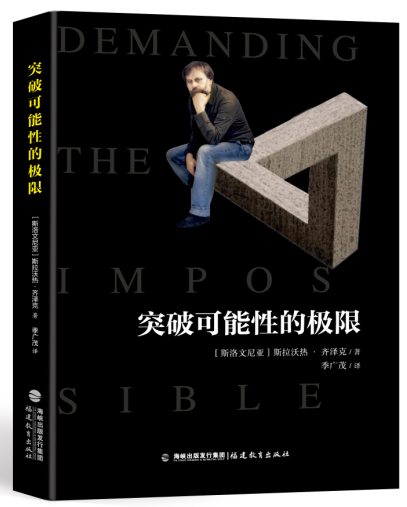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