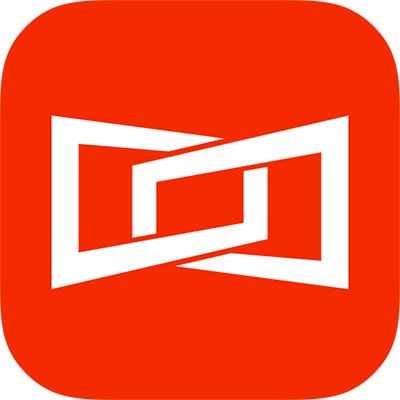“我也想养更多的孩子,但我继续做母亲的权利却被人无情的剥夺了。做不做母亲应该是我来选择,而不是他们!” 维多利亚愤怒地说道。
1996年,维多利亚怀上了第三胎,感到身体不适便到医院做检查。
“当时已经怀孕32周,我的医生决定将我送往急诊室,进行紧急剖腹产手术。”维多利亚回忆时说道,孩子由于早产肺部发育不全,呼吸困难,没多久就夭折了。
身旁的朋友不断安慰维多利亚:“没关系,你还年轻,还会有下一个宝宝的。”
但医生的话却如晴天霹雳一般:“你已经无法怀孕了,我们给你做了节育手术。”
那年,维多利亚仅仅32岁。

在1996-2000年间,约有30万女性被迫节育。这都“归功于”时任总统阿尔韦托·藤森的自愿手术节育计划,旨在摆脱贫困,以家庭为单位的计划生育。
1997年,维多利亚开始了与政府的斗争:“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权利,这是国家政策的一部分,涉及到的女性更是不计其数。”维多利亚谈道,“全秘鲁的医生不经女性患者的同意,便可以擅自做出节育的决定。”
2003年,经过数年司法斗争,维多利亚为自己争取到了约2000英镑的赔偿金,也是唯一一位因被迫节育而获得赔偿金的女性。
通常,被节育的男性和女性多处于贫穷阶级,说着本土的克丘亚语,他们在手术前签下的同意书也是用不认识的西语。
时任总理滕森表示,贫穷阶级计划生育是一项长期计划,提供包括节育手术在内的多种节育方式。但无论何种方式,此前节育在秘鲁就是违法的。

Quipu组织成立之初便是为了聚集更多像维多利亚一样成为自愿手术节育计划受害者的女性,并将她们的遭遇分享给更多的人。
组织负责人罗斯玛丽·勒纳表示:“表面上说是通过多种节育手段推进项目,但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是有指标的,节育手术要达到一定的人数和比重才行。”

Quipu是一种古老的绳结记事方式,“我们以Quipu为象征物,希望记录更多的口述信息,唤起集体女性的记忆,被迫节育的惨痛经历不能忘记。”Quipu组织的网站上如是写到。

加入Quipu组织的受害者们,在秘鲁可以通过免费的电话热线分享自己或是倾听他人的遭遇。她们的遭遇会被译成克丘亚语、西班牙语和英语上传到网站上。
勒纳的团队经常奔波秘鲁各地,教会当地的受害者如何分享他们的亲身经历。目前团队正在亚马逊丛林区内进行宣传培训。

“大部分的故事都很相似,医护人员如何各家各户地寻找待节育女性,如何糊里糊涂地做了手术,术后多么悲痛,有些女性怀着孕也被迫进行手术。”勒纳说道。
有时手术过于粗糙简陋,不会实施全身麻醉,许多女性术后都留下了永久性的伤害,无法生育,也让她们觉得失去了自己的社会价值。
时至今日,被节育依旧是许多女性不愿提及的往事,勒纳和她的Quipu组织就是为了扭转这一错误的认知,要勇敢站出来,说出自己的伤痛,让女性们知道,她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目前,依旧有许多受害者在等待着一个公道的判决。
维多利亚承认,她拿到赔偿金的部分原因是她并非来自贫穷阶级,她是一名受过教育,能说西班牙语的中产阶级。
“我们要的不仅仅是赔偿金,我们要的是司法公正的审判,能够正视历史的真相。”维多利亚说道,“针对穷人和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替他们做决定,这是一种种族歧视。在21世纪,怎么能这么对待女性呢?我们要将决定权掌握在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