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社会理论界的原子弹爆炸”,在《人类新史》中文版新书发布会上,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梁永佳对此书这样评价,称这本书会导致“很多学科重新思考自己的开始”。
《人类新史》的两位作者是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和考古学家大卫·温格罗。大卫·格雷伯于2020年去世,在他去世的三周前,他和大卫·温格罗共同完成本书。书中指出,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丰富的、多方向的社会实践,但是在历史的演变中,多样性、多变性、灵活性都在消失,人类逐渐陷入了单一固化的模式和秩序。这本书的写作耗时十年之久,用大卫·温格罗的话说,是“一次试验、一场游戏”,“一个人类学家和一个考古学家尝试重构有关人类历史的宏大对话”。二人合作,通过考古学和民族志的细节和人类学理论,一方面审视考古学的研究发现,另一方面考察世界上不同区域、族群的社会文化和组织方式,以“恢复我们祖先全部的人性”。
在发布会上,大卫·温格罗谈到,格雷伯最喜欢的哲学家罗伊巴斯卡尔(Roy Bhaskar)一句话是“清扫人类思想的枯叶”,这句话指的是定期扔掉那些伴随真正科学进步产生的哲学垃圾。如果任其积累,这些垃圾就会成为我们增进理解的障碍。温格罗谈到,在《人类新史》中,二人就试图清除那些关于不平等的研究产生的“人类思想的枯叶”。

人类政治体系中存在惊人的多样性
“大多数关于不平等的大理论和大思考,都始于人类从一个想象中的平等的、天堂般的自然状态堕入了一个不平等的世界。不平等是由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带来的必然结果,根据人类历史的标准叙事,即使面对致命的危险,也无法挽回这一事实。”温格罗谈到,在《人类新史》中,最重要的新问题是,不去讲述一个关于人类物种是如何从田园牧歌般的平等的自然状态而堕落到不平等社会的故事,而是去问我们究竟是如何被困在这样一个如此严厉的观念枷锁当中,以至于我们甚至再也没有办法想象重塑自我的可能性。 在书中,作者展示出了人类史前时代的新画面——既不同于卢梭式的纯真状态,也不同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而是充满创造力和能动性的人群在决定自身何去何从。以此画面为基础,《人类新史》展现了人类文明的新进程,这一进程不以文字、城市、国家等的出现和发展作为文明的主要标志,不再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作为全人类的未来。

温格罗说,对美国政治家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共同批判是他和格雷伯对话的起点。在二人相遇之前,分别写过对文明冲突论的批判。格雷伯写过《“西方”从未存在过》,书中谈到,民主本是一种各地都存在的历史悠久的实践,它是在全球化系统形成过程中结晶化,却逐渐被统治精英所采用。它在西方经历了“收编”和“重构”的进程,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一种“西方传统”——吊诡地将民族国家的宪政制度嫁接到古希腊民主之上。事实上,不只是民主不发源于西方,这个收编与重构进程本身甚至也是并非西方所独有的。大卫·温格罗也写过《什么造就了文明》,书中谈到,文明不是孤立形成的,而是通过社会之间的文化混合和借鉴而形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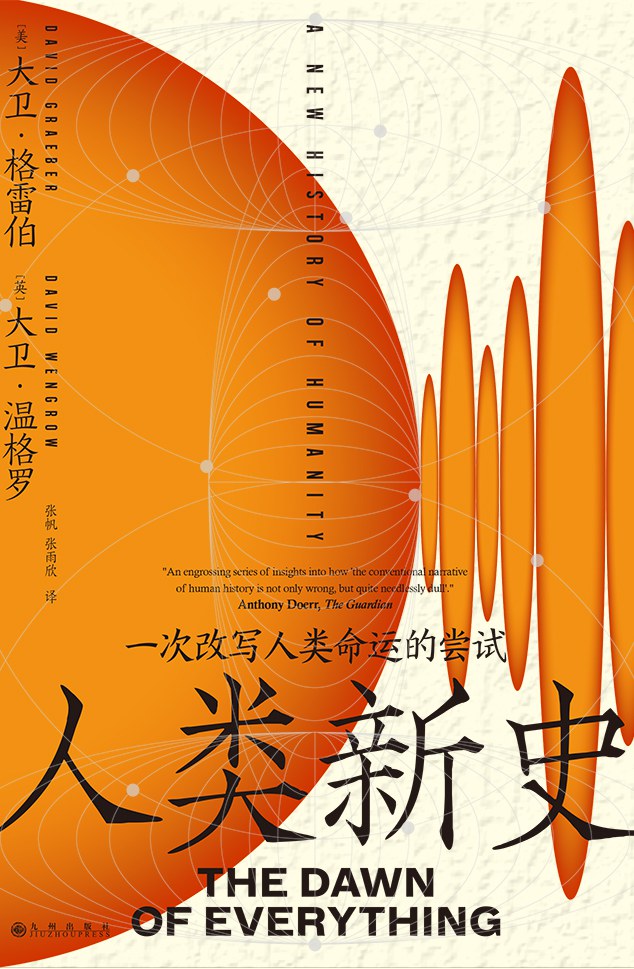
[美] 大卫·格雷伯 [英] 大卫·温格罗 张帆、张雨欣
后浪·九州出版社 2024-9
温格罗强调,他们并不是对多样性进行无限制的赞扬,也不是赞扬相对主义,而是想要建立新的比较框架。在书中,二人谈到了三种自由:第一种自由是离开的自由,第二种是不服从的自由,第三种是重新组织社会关系的自由。本书译者、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张帆说,第三种自由指的是人们可以选择一群不同的人,用不一样的生活方式重新组织我们的社会。在世界上,人人都在追求幸福,对于幸福有各种各样的理解。世俗化的理解是我们要有足够有钱,足够强壮,但对于格雷伯和温格罗来说,即使在很悲惨的情况下,依然知道有人随时会施以援手,这种才是终极的幸福。第三种自由就是这种幸福实现的前提保障。
文化系统会对相邻的社会进行有意识的排斥或者逆转,因此人类政治体系中存在惊人的多样性,也因此,人们需要对“革命”进行新的理解——人类经验中的社会变革更像是一种玩耍。张帆说:“我们不光玩农业,我们还玩国家、玩城市,对各种各样的历史发展的关键结构,以一种玩的精神面貌,重建拆毁再重建拆毁,来充分实现我们对于幸福的想象。”张帆认为,尤其是在当下社会性抑郁的情况下,人们好像失去了玩的能力、失去了玩的可能性,不妨把“玩耍”的概念重新运用到个人生活中去。

中国考古学家需要书写自己的大历史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看来,他对这部著作的不满意之处在于,全书征用了全世界几十个文明的资源,唯独提到中国时只有一两句话。他说其实不论是从人口的规模,从社会和文化的规模,还是从历史时间的跨度来看,中国都是一个巨大的时空存在,去掉中国,这个世界就少了四分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常怀颖也认为,本书对于中国农业的讨论尤其是对南方地区稻作讨论的缺失是一种遗憾。他谈到,因为用英文撰写的中国上古时期综合性考古材料的缺失,导致英语世界描述文明多样性时往往会忽略远东地区。常怀颖谈到,其实,稻米能够支撑起的人口数量异常庞大,而且稻米的驯化与近东地区的小麦驯化不一样——近东地区的小麦基本上是集中在新月沃地这一个地方开始驯化的,然而,水稻的驯化却出现在许多不同的山间小盆地之中。而且种植水稻的人往往不愿意迁徙——水稻的种植包括了算计和经营,需要计算什么时候插秧,什么时候去收获,什么时候放水,什么时候把水排干,这一点和旱作农业当中种植小麦、小米的思路完全不同。
常怀颖认为,中国考古学界在近年来已经指出中国上古时期存在很多不同的社会样态——红山文化的万物有灵;黄河中游到下游以农业生产为基础带来的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结合的社会状态;长江下游以良渚文化和石家河为代表的,可能基于一元神信仰的宗教和军事集团结合的状态……不同的状态到了商代时,差异才慢慢消失,“大家都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去。这种目标可能是远东地区基于农业社会的一种基因。”他认为中国的考古学家需要书写自己的大历史,以丰富世界文明史的样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