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期主持人 | 尹清露
整理 | 实习记者 丁欣雨
无论你是否追星或者混二次元,都可能听说过“梦女”。梦女来自于日语“夢女子”,是指幻想与二次元人物恋爱的女性。随着这一群体的扩大,近两年也出现了三次元男明星和偶像的梦女。与“女友粉”不同,梦女代入的并非对方的女朋友,而是创造一个虚构的路人角色来代表自我,与对方展开幻想的浪漫关系。
如果你看过小红书或微博上的梦女文,就会发现,梦女与女友粉更微妙的区别在于,前者往往强调一种爱而不得、飞蛾扑火的卑微感,也正因卑微使她们的爱显得格外梦幻,行文中多是“阵雨、便利店、烟灰缸、蓝色毛衣”这类潮湿又伤感的意象。微博投稿bot“@我都梦女了你让让我”中有一篇被奉为神作的梦女文,就描述了自己追韩国idol时,同担已经跟idol谈上恋爱的悲伤故事。前两年更主流的话语还是“不要恋爱脑”,但现在我们似乎对沉浸于幻想恋爱的女性有了更多理解,其中存在有趣的心理状态转变。
最近,国内几名rapper公开diss乙游中的女性是“被毒害的孩子”,认为手机里的伴侣“并不是爱情”,引发了众多乙游玩家的讨伐,指责他们对女性爱情想象的刻板和单薄。

关于梦女,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同性梦女文也很受欢迎。比如想象女团NewJeans成员姜海粼是“那个温柔的高中同桌”,孔雪儿是“老家的邻居姐姐”,文章聚焦的都是光彩夺目的女偶像成名之前的平凡故事。这似乎也意味着,女性的情感投射不一定总是指向性缘、慕强和霸道总裁,它也可以指向女性之间的互相体认。
01 梦女的矛盾情感小传:心怀卑微,保持距离

董子琪:我想到一首歌《追光者》,歌词挺贴合梦女的心态:“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连眼泪都觉得自由/有的爱像大雨滂沱/却依然相信彩虹”,还有强调我是渺小卑微的,“你是光,我就是影子”这样一组关系。
如果说梦女是新现象,那么能对应的老作品是《大宅门》里的角色白玉婷(蒋雯丽 饰),她疯狂追逐着唱戏名角万筱菊,已经超出粉丝对偶像的爱,甚至想要嫁给他。白玉婷举行了一场正式婚礼,把自己装扮成新娘,嫁给了万的照片,又在新房里摆满他的唱片。但在白玉婷真正打动了对方,他想要跟她结婚时,她又拒绝了。

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心态,仿佛跟偶像的距离太近就会沾上落下来的金粉。之前看到批评说女性不懂得区分真与假、阅读和消费,批评女性都是包法利式的读者,读一本书就是要吃掉它,追一个偶像就一定要想象自己占有他,吸收关系里的浪漫情愫。我反而觉得,梦女是需要对真人和光环以外的世界保持距离的,照片、唱片和虚假的关系把她隔绝在更完美安全的世界,她不愿有人来打破这面墙。爱上角色而非真正的人,这种狂热和投入来源于经典的魔力,角色的生命力有可能大过个体现实中的一生。
尹清露:我也发现梦女的心理状态往往很焦虑。她们焦虑于没法真正见到自己爱的人,对方永远不知道自己的存在,但她们又沉浸于痛苦潮湿的爱恋之中。
小说《梦女》最近推出了中文版,作者是一位美籍韩裔女性,写的是女主角怎样从一个韩国男团的路人粉步步沦陷,变成毒唯的过程。书的原名叫做《Y/N》,也就是your name的缩写——在同人小说中,读者可以代入自己的名字,跟现实中无缘见到的明星展开共同的经历。这是一本荒诞、有些哲学意味的小说(这个暂且不提),但许多部分确实是梦女的心声,带有一点绝望和悲伤。其中有段话非常符合梦女的心态:
但他们不会并排走,在街上,她始终跟在他身后,隔开几米的距离,这样就能一直对他保持渴求。他们已经达成相爱的共识,却推迟了在一起这件事。他们总共见了17次,才开始触碰对方。

[美] 埃丝特·李 著 张悠然 译
中信出版社 2024-7
徐鲁青:梦女和女友粉的区别在于,梦女需要二度创作。我追星的经历很少,接触的大多数是同人方面的女友粉。女友粉较少去设想全新虚构的自己,梦女则不会直接代入同人文本,她们需要在原作的世界外凭空虚构一个角色,再用这个角色和男性恋爱互动。
“BIE别的”公众号发过一篇文章是梦女的自述(《梦“女”的梦女:“陈都灵是我少女时期的英雄主义”》),那个女生说,固定文本里的女性角色创作得比较扁平单一,她觉得不符合想象中的自我,所以需要创造角色来表达个人感受。梦女的重点也许不在偶像身上,而在自我身上。
有个反例是《阅读浪漫小说:女性,父权制和通俗文学》,书中也有谈到女性幻想的成分,但将女性读浪漫小说归纳为父权制的驯化。女性的恋爱情结无法在异性恋关系中得到满足,她会把自己代入到浪漫小说里,把男性的冷酷无情和虐女行为解释成浪子:他总是一往情深、满腔柔情,但他的爱最后只对一个女性显现。和梦女不同,前者是代入浪漫小说的框架里,通过曲解对方的意图让现实更好受。梦女更有主体性,她们创造自己的形象,并与自己的欲望对象互相生发出想要的感情。

尹清露:感觉像一种阶段的进化。在我们90后小学初中的时候,没有梦女这个词语,但是梦女的情绪很流行。那时最流行的是磕cp(couple),我磕的是动画《钢之炼金术师》里的男女官配,爱德华和温莉。我可以代入梦女的部分在于,我觉得爱德华是一个不存在但胜似存在的人——他虽然不存在,但比许多存在的人都要重要和真实。我磕cp磕得很开心,也完全不想要代入自己。但当时有一点代入自己的做法是大家会找语c(语言cosplay),找一个现实中的人跟自己搭档,分别扮演角色,再把情感投射在搭子身上。但是最近几年,二次元圈出现了“同担拒否”这个词,大意是拒绝和粉同一个人的粉丝交流或接触,也有许多梦女一想到这么多人都爱同一个人就觉得崩溃。我对这一点感到很惊讶,感叹粉圈的气候变化之剧烈。
潘文捷:但凡是人,都会感到自己渺小脆弱,特别是在现在如此不确定的世界,人是具有造神冲动的。《娱乐新闻小史:从讲八卦到流行文化的诞生》一书把名人分为四类:电影明星、电视明星、真人秀明星、网红。电影明星和其他明星的逻辑不同,在其中占据类神的位置。看电影是一种仪式,要先看排片、选座位、约同伴、空出时间,才能有进入影院的资格。观众受到电影的召唤而来,在一片黑暗中仰望巨大的银幕。电影银幕上的图像在观众前方盘旋,它不受观众的控制与改变,是遥远的、不可接近的、令人着迷的既定存在。
与此相比,电视明星的核心资产是亲密性。看电视是随时能发生的日常行为,特别是连续剧或系列剧,每天固定时间见面,错过了这个还会有另外一个。电视听候观众的召唤,人们可以选择电视机的大小和摆放位置,各个设定都可以由观众掌控。电视明星就像待在电视盒子里,只要按下遥控器就可以日复一日地出现。但如果想了解电影明星,只能通过额外的付出,比如买杂志、追采访、收集周边来实现。所以在此前,电影明星是神一般的存在,而电视明星,包括后来的真人秀明星和网红,都更接近于平时生活中看起来很有亲切感的普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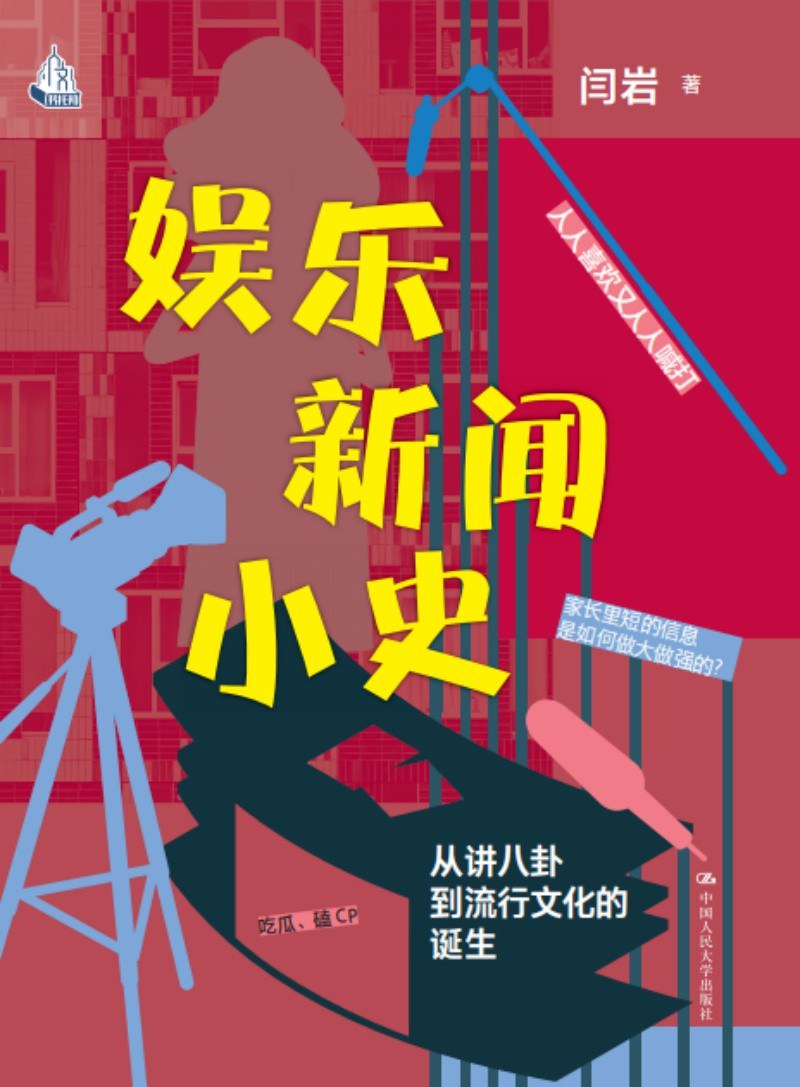
闫岩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4-4
但是这本书也讲到,由于媒介发生变化,“网红逻辑的殖民”正在发生。哪怕是电影明星,现在都要变成网红。他们需要在微博上发布自己的消息,分享生活,仿佛在日常就能被人们接触到。大多数人很需要这种亲密的存在,但还是有部分需求是去仰望一个神的。梦女的卑微心态和保持距离符合这类需要,在几乎所有明星都已经离人们那么近、他们的消息唾手可得的情况下,自己造神是有可能的。
子琪说到,角色的魅力大于人的魅力,我觉得保持距离是渴望安全的表现。以前我们在传统媒介上看明星时经过了一层过滤和把关,我们无从知晓明星的真实状况,但现在明星随时随地都可能塌房。近期播出的《脱口秀和ta的朋友们》节目里,于贞讲到rapper塌房的定律是“塌男不塌女”,其实撇开说唱圈也是如此。如果喜欢的神那么容易塌房,安全感就完全不存在了,这时自己去造个神会是更安全的做法。
尹清露:文捷刚刚说的矛盾非常有意思。我们一方面想保持安全距离,把他当成神灵,另一方面,现实中网红逻辑的殖民又不允许真的把他当成遥远的神,因为现在很多idol的逻辑都是要进行亲密的互动。
我追NewJeans的时候发现,idol会跟粉丝聊天对话。粉丝发几条消息,对方就会在粉丝的留言中挑选回复,对话页面非常像微信。这种刻意为之的亲密感给人以错觉,以为她们就是身边的人,但心里又明白,自己无法跟她们有任何真正亲密的接触。

我还刷到很多关于“梦女心态如何调理”、“如何治自己的梦女病”的帖子。病症表现为很想接触到“梦角哥”(常用缩写mjg来称呼,指的是爱上的男性角色),但又接触不到,就会采用一些不同的方法,比如通灵。有人说强迫自己感受梦角哥的头发,然后就真有种摩挲头发的感觉。
我看到一个说法:女友粉虽然想和对方谈恋爱,但自知只是对方的粉丝;梦女自知只是对方的粉丝,但就想和对方谈恋爱,颇有种不管不顾的感觉。女友粉对于明星的喜欢还在所谓合理正常的粉丝框架中,但梦女有疯狂的性质。还看到一句话是说,“如果你(梦角哥)不幸福的话,我会为你难过。但是如果你太幸福的话,我又会嫉妒你。”这种矛盾纠结的心态跟子琪写过的“鼠鼠文学”(《鼠鼠我啊,在蜗居的岁月里包浆》),还有我自己盘点亚文化时讲到的“厕妹”(《卑微戏谑,搞搞玄学|2023年网络文化盘点》,厕妹是很多青春期女性会把微博的一些投稿bot当作厕所,常去那里抒发自己爱而不得的状态)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梦女》中的女性角色与《我要快乐!当妈妈们开始追星》的作者塔比瑟·卡万(《当一位失落的妈妈迷上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专访》)非常不同。《我要快乐!》归根结底是直线型叙事,一名中年女性从认为追星羞耻,到逐渐地放开,承认自己很快乐。但梦女有一些欲望,有爱而不得的失落,失落中有怅然,最后又感到无畏,这是更复杂的情感结构。
02 幻想的力量:习惯枯燥?假装坚强?拿回玩耍权!
林子人:我对梦女的理解并不局限于一种想象的爱恋关系,它归根结底是女性在一个情境里尽情释放幻想的行为。回想童年,我在小学或初一的时候算是《魔卡少女樱》的梦女。我想象自己也是一个魔法少女,是小樱的朋友。后来魔卡少女出了新的Clear Card系列,真的有个类似的转校生角色,是个叫秋穗的女孩子。
女性需要有这样的空间去尽情释放幻想,这种幻想能够一定程度上帮助形成自我意识、个人的身份认同,或者自己的某些性格。幻想并没有跟现实完全脱离,它其实就存在于现实中,成为塑造自己人生道路的一部分。
《我要快乐!》援引了精神分析学家埃塞尔·S·珀森的《幻想的力量》(By Force of Fantasy: How We Make Our Lives)一书。在那本书里她提到,幻想、白日梦、遐想、内心戏以及性幻想,并非无所事事时的消遣,它们在现实生活中能够抚慰、唤醒和塑造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关注脑海中天马行空的想法,即使它有时让人感到尴尬或者羞耻,但其实影响着我们的现实生活,有时甚至带来根本性的变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4-6
作者采访了很多其他从事同人创作、深度介入粉丝文化的女性,提问她们理解的粉丝文化到底是什么,其中有个回答是:和工作完全相反,参与同人创作是一种不求回报的给予,一种分享的快乐,一种玩耍的乐趣,不需要考虑补偿。那位女性还说,一旦我们长大成人,就会彻底放弃玩耍这件事,但所谓新教徒式的工作理念纯粹是用来唬人的。因此粉丝文化的核心在于重新夺回玩耍的空间,允许自己保持有益的自私。参与粉丝文化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分配时间,不用考虑什么是最有效的,或者什么是对他人最有利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成为梦女,允许自己沉浸在梦女的幻想当中,其实是一种玩耍,而且是完全只关注自己内心需求的行为。在女性的成长过程中,因为社会身份在变多,责任在变多,他人的要求在变多,这种时刻会随着年龄的变大越来越少。做梦女像是对这一事实的反抗,潜台词是说,我需要保留一段只属于我自己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做什么都可以。
董子琪:这其实可以两说。我婆婆喜欢看霸道总裁的言情小说,晚上很多时间都花在这些小说上。她白天很操劳,做各种家务,安排妥当所有东西。一方面,夜晚的时间段完全属于个人,可以游戏玩耍,投射浪漫想象,但另一方面又是一种缓释,能让自己更加好地回到的白天的生活中。但如果把释放点完全固定在单一的、也没有特别延展性的故事当中,是不是有点可惜呢?梦女也许也是这样一种需要不断回到场景中、持续追逐、高度重复的行为。
前一阵听梁静茹的《爱久见人心》,里面有强烈的虐恋倾向和彼此间高度不对等的关系。“你的孤单是座城堡/让人景仰却处处防疫......我不是流言 不能猜测你/疯狂的游戏 需要谁准许/别人怎么说 我都不介意/我爱不爱你 日久见人心”,她非常想把自己投入到一个略带政治性的commitment,就像《离骚》中屈原对楚国君王的许诺一样。可能有很多非议使彼此关系变得脆弱、不可信任,但相信真心的时间够久就会被看见,这种剖陈心迹的感觉挺值得玩味。后面还唱到“存一寸光阴 换一个世纪/摘一片苦心 酿一滴蜂蜜”,虽然现在外人看来会觉得何必呢,为什么非得用苦心酿蜜来证明自己呢?但我从中感到歌曲的流行跟整个社会气候是有关的。

徐鲁青:前段时间,梁静茹在演唱会上哭着表达类似“一直没有找到爱的人”的话,当时微博上很多人骂她不够大女主,不理解为什么成就那么高,还在需要被人爱的事情上伤感。现在看来这首歌唱的是不顾一切的爱,之前是流行的,但现在就被人批评,大家对梁静茹的反应确实能体现社会趋势的微妙转变。
03 女生们的反抗:亲密关系领域的思想实验
潘文捷:学者高寒凝指出,很多同人小说以亲密关系乌托邦的幻想世界为背景,文本的核心特征是对亲密关系的探索。磕cp,给角色配对,其实是女性在进行一种思想实验。这种思想实验规模很大,但几乎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大比率男性深度参与,而是在女性社群内部展开的、针对亲密关系的自由探索,是女性社群成员对亲密关系需求和性需求的自我满足和相互慰藉,这构成了对父权制的冒犯。与之相比,梦女并不参与大家的配对,而是自己完成配对过程。但统一的是,以上两种恋爱都不需要真实存在的男性。被说唱歌手diss的乙游里完全就是纸片人,好像更是对真实存在的男性的放弃。
上野千鹤子和铃木凉美讨论时说,女性对于亲密关系的学习是通过浪漫爱情小说实现的,男性则通过AV,两部分人的话根本说不到一起去。很多网上的帖子也都表现出女性在寻找亲密关系的过程中对真实男性的幻灭。她们只能依靠自己来进行亲密关系的思想实验,一方面有些可怜,另一方面也情有可原。看到rapper的diss,我也感到很难受,双方完全没有在对话,要么是回避对话,要么是直接攻击,不就原因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只是口诛笔伐而已。
尹清露:说唱歌手diss乙游凸显了双方对话的不可能,确实很可惜。虽然一些人会谈到男女对立,男性和女性对于爱情的想象不同,但作为人的情感,以及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某些绝望感受,是基本共通的。我想到河南说唱之神的《冷漠女人》,讲的是他爱上一个坏女人,那个坏女人玩弄他于股掌之间,抛弃他以后的忿恨感觉,他在歌词里唱到“你是个cold a f bitch”(你这个冷漠的碧池)。这种对于情感的执著、对人与人连接感的渴求是共通的,但如今在讨论的语境中完全错开了,我觉得很可惜。

刚刚子人提到《我要快乐!》和《幻想的力量》,可以顺带连接到对于梦女与自我主体性关系的疑问。梦女的出现质疑了所谓大女主或独立自我的必要性。“BIE别的”公众号另一篇文章《“我觉得NewJeans是一支伟大的女团,但我没有证据”》,说的是NewJeans之所以能够火到出圈,是因为她们跟之前像BLACKPINK那样很girl crush、强调女性主体力量的女团不一样。NewJeans望向自我主体性并未完全成型的那段青春期,这几个女孩也不是可以仰慕的姐姐或者学习的榜样,而是亲切的邻居和朋友,在她们身边不需要担心自己会出糗。
主体性的说法本身带有男性本位的色彩,人们需要保持理性才能隔绝周围的一切,把自己当作主体,把他人当作客体,也因此产生凝视与被凝视的关系。但是塔比瑟·卡万和其他女性作者要讲的是,其实我们要追回的、其中包含想象的快乐,是非理性的,也许其中并不存在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对立。
《我要快乐!》中有个段落是卡万对一位文学女教授的采访,那位教授同时也是同人作者。卡万问她平时会不会跟同事们说自己是个同人女,她哈哈大笑说当然不会,因为学术界很排斥天真透明的理想主义,它只提倡怀疑主义和理性的批判。女教授认为这是一种男性的思维方式,男性总在掩盖自己的情感维度,女性也不得不遵守这个标准。从这个角度来说,梦女也的确是一种具有反抗性的行为。
04 同性梦女文:不止爱情,更关乎理想的人生范本
林子人:微观史作品《江户时代江户城》的作者是美国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艾米·斯坦利,她偶然在网上看到了一些书信,书信往来的主人来自一位生活在19世纪日本幕府末年越后地区的乡村女性常野和她的家人。作者花了大约十年时间走访和查阅资料,最后还原出了常野的生活。常野出生在一个僧侣家庭,三次婚姻都以离婚告终,在长兄想要给她安排第四次婚姻时,她随人偷偷跑去江户,自立门户,追逐梦想中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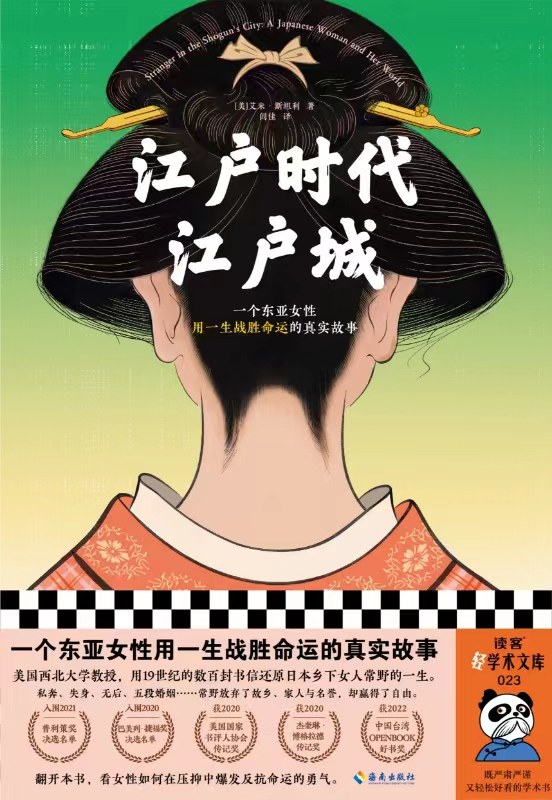
[美]艾米·斯坦利 著 闾佳 译
海南出版社 2024-1
作者写到,在19世纪,像她这样的日本女性童年时代会阅读很多特别针对女孩编写的初级读物,例如《女大学》《女大学宝箱》,其中《女大学宝箱》为11世纪的名著《源氏物语》里最著名的一些章节绘制了不同版本的插图。总的来说,这些女性读物里的插图都在讲述不同女性的故事,其中有《源氏物语》中穿着精美和服的女官,甚至会出现中国古代的美女。斯坦利在书中暗示,这些距离自己日常生活非常遥远的女性的故事,或许正是对女孩常野想要逃离婚姻,去日本第一大城市江户过上不一样人生的激励。
这大概就是一个19世纪日本梦女的真实案例吧。如果不局限于亲密关系和浪漫爱情,梦女这种社会现象的核心本质,是否正是对于某种跟自己日常生活截然不同的、更美好生活的想象呢?这样的想象从古至今对女性而言都非常重要,因为现实生活面临太多限制,我们需要不停寻找理想女性的摹本,在想象的世界里看见更多可能性。这种心理机制跟我们聊白女的那期节目(《承认吧,我们都有过憧憬“成为白女”的时刻|编辑部聊天室》)里提到的也有点类似。
尹清露:很多同性梦女文都在写女明星成名前的故事,成名前大家本质上是同样的人,她去了更闪耀的地方,意味着我们也有可能去到那,而其中隐隐的失落感就在于,我们还没有到达那个地方。
不止于异性恋,同性梦女文拓宽了一个维度,向往情绪的投射对象是那个“想成为而难以成为”的更好的自己。有点伤感和残忍,其中又有潜在的想象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