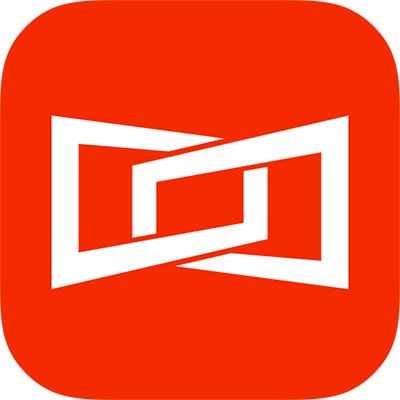作者:Laura

人们在谈论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时,谈论最多的当然是他那两部反抗极权的反乌托邦小说,《动物庄园》(1945)和《1984》(1948)。更多的人被《1984》里面非人性的空气所窒息。
但是,我很想知道,创作了悲惨无望的预言式作品的奥威尔,在他47年短暂的生命中,有没有某个幸福的时刻呢?哪怕是很短的瞬间?写完一部长篇小说之后他应该有那种成就感吧?
人到中年时有没有“岁月静好、一切尽在把握之中”的感叹呢?他那惯常的犀利的眼神,有没有过温柔的一瞥?我一定要在他“处处显得不自在”的生活中,找寻几束幸福温暖的光线。我把奥威尔的生活逐层剥离,又用手执放大镜的办法,从他满是荆棘的人生道路上,捡拾他快乐的种子。

奥威尔少年时代的寄宿学校的经历,对他后来的人生轨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于1903年出生在英属印度孟加拉邦莫蒂哈里,他的父亲在当地殖民政府做一个小官员,一辈子都是在捉拿鸦片贩子。他说他的家庭属于“上层中产阶级偏下,即没有钱的中产家庭”。奥威尔8岁的时候考入了英国的一家叫圣赛普里安的寄宿学校,可到了学校不久,就开始“尿床”了。
现在看来,8岁的孩子尿床的原因一定跟刚刚与母亲分开,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有关系,但是那时候的寄宿学校哪里会去照管孩子的心理发育?后来,奥威尔在回忆他的童年时说,他的童年有“一种凄凉的孤独无助的感觉,不仅给锁在一个充满敌意的、邪恶的世界中,而这个世界的规则是我所无法照办的。”
他发现学校为了考虑名声,一方面招收才能出众的中产家庭的学生,给他们奖学金,送他们去哈罗和伊顿;另一方面又吸引有贵族头衔的少年。而学校对这两种不同的学生区别对待,这一点让奥威尔深恶痛绝。
他对圣塞普里安寄宿学校所能记住的,是劣质的伙食、鞭挞惩罚、以及校长的势力。在这所学校,他被分配到专门学“没用的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天才班,借此他考上了伊顿公学的全额奖学金,但是他后来说,他在伊顿“没有用功读书,学到的东西很少”。
一战之前的英国,阶层差别是赤裸裸不加掩饰的。这个敏感的英国少年,从学校教育中得到的都是积攒已久的怨恨。
我不甘心,找了又找,终于在奥威尔的童年中找到了一点点和学校有关的温暖记忆阳:“在夏天的下午,有时穿过丘陵地带到一个叫比林口的村庄或者到海滩尽头去远足,是很好玩的。我们可以在石灰岩的岩石中间冒险游泳”。……
“还有在夏天的早晨很早醒来,在阳光已经照了进来,但大家还熟睡未醒的宿舍里,不受打扰地读一小时小说的快事”。……
“在一条没有人迹的支线上坐两三英里的火车,手里拿着绿色的大网来回奔跑追逐一个下午,在草尖上飞翔的美丽的大飞蜥,气味熏人的杀虫瓶,然后在一家酒店的店堂里坐下来喝茶,吃大块淡颜色的蛋糕。这一切的关键是火车旅行,因为它似乎在你和学校之间造成了神奇的距离”。
我是多么迷恋上面的这些文字。这么单纯的描述,不需要增添任何的修饰,就足以让读者见到这个男孩难得的欢愉。这个描述中有颜色,有气味,有茶点,有阅读,这一定是奥威尔记忆中最深的幸福之一。

从伊顿毕业后,因为成绩平庸,奥威尔没有得到牛津剑桥的奖学金,他只能去投考公务员,报名去了缅甸,在当时的印度帝国警察服役。这段经历给奥威尔造成了至少两点不可挽回的后果:其一,缅甸湿热的气候毁了他的健康,其二,他发觉自己在不知不觉中感到英帝国的统治很大程度上是个大骗局。因此,他辞了职,怀揣着写作的梦想,来到了当时的文艺之都巴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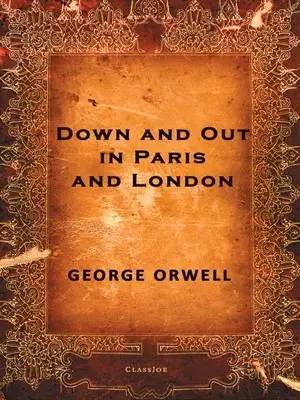
奥威尔在《巴黎伦敦贫困潦倒的生活》里,依然用了类似白描的方式,讲述了他在巴黎贫民窟的生活。他常常饿着肚子几天没有东西吃。但一旦时来运转有了点钱,就会去小酒馆喝个大醉快活快活。
他说贫困是个丑陋的经历。他把洗盘子的工作比作“奴隶”的工作:这么一天17个小时没有喘气的工作,让人没有思考的机会,只有“满足感”。
他说:“这是一种深深的满足感,是那种吃饱喝足的动物具有的满足感。生活因此而变得如此简单。”因为害怕这个“为了制造没有必要的奢华,而不得不做的,没有意义的工作”会毁了他的意志,他决定离开。
对于奥威尔的这段经历,读者们都被他的贫困吓呆了。他偷偷摸摸去当铺当衣服,他饿着肚子躺在床上看着害虫慢慢地在墙壁上爬行,他不见天日地在地窖一般的后厨洗盘子,这些描述都让人难过。
但是我还是如愿以偿地在字里行间找到了一点点的平静。他和他的俄罗斯朋友的友情,是他在贵族学校和缅甸当警察的时候不曾有过的,他们奔波忙碌,一天没有进食之后,还能一边抽着烟草,一边在纸上对下国际象棋。据说,只要有了象棋,就不会觉得肚子饿了。
他在巴黎的贫民窟遇到了很多不同国籍不同民族的人,人们似乎并没有像贵族学校里的学生那样,分出个等级差别。因为大家都没有钱。虽然奥威尔没有说,但是我看得出,他的这段极度贫困的阶段,似乎比他在伊顿的时候,更加自在。而那些贫困,那些饿肚子的往事,都如烟了。况且,经历过那样挨饿的生活,还有什么是他不能忍受的呢。
当他回到英国,开始专业写作的时候,奥威尔慢慢地开始过上了想要过的生活。但是他依然充满了牢骚和抱怨。他写过《一个书评人的自白》,开篇就描述了这样的场面:“在一间寒冷而且憋气的坐卧两用的屋子里,到处都是烟头和喝了半空的茶杯,一个身穿满是蛀洞的睡袍的人坐在一张摇摇欲倒的桌子旁,想为他的打字机在乱纸堆中找个地方放下来。……
他年约三十五岁,但看上去已像五十岁的人了。他已经谢顶,青筋毕露,目戴眼镜,…… 如果情况正常,那么他就会患上营养不良;如果最近交了好运,那么他就会因为饮酒过度而头痛欲裂。…… 不用说这个人是个作家。”
但是细心的读者,在他牢骚和抱怨的文字下面,能读到他的平静。在《为英国式烹调辩》里,他教读者们烧土豆的方法,“你在哪里见到过土豆放在带骨的腿肉下面烤?这种烤法是最最好的烤法”。在《泡一杯好茶》里,奥威尔教大家最佳泡茶方法的十一条金科玉律。在《英国式谋杀的衰落》里,他对报纸上读来的英国谋杀案津津乐道。这些也是他逐渐脱离贫困之后,可以享受到的一点点的平静的生活。
奥威尔依然不富裕,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肺炎折磨着他;他依然牢骚满腹,也依然自恋;依然犀利,尖刻。但是读者也能看到他的温暖和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