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展开,以白话文撰写的、不受格律限制的“新诗”取代“旧诗”,成为了诗歌写作的新风向。当时,创作新诗的目的就是否认旧诗是诗。一系列被称为文化先驱的新人,包括周作人、鲁迅、钱玄同、李大钊等,无不例外开始新诗的创作,但热潮过后,这些诗歌却没能留下太多影响。沈从文曾在文章《新诗的旧账》中梳理新诗发展的历史,对此,他毫不客气地表示:“把这些人的名字,同新诗并举,如今看来似乎有点幽默了。”由于初期新诗在内容和形式上不设任何规范,几乎一切分行皆可称为“诗”,所以就数量而言,新诗的成绩是不小的,但就质量而言,沈从文认为“多数诗都太杂乱、太随便、太天真”。
对于读者而言,沈从文在小说、散文以及历史文物研究方面的成就早已十分显著,但事实上,他与新诗的关系更为密切和持久。自上世纪20年代起,沈从文就是新诗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他不仅自己写诗,还致力于新诗的批评和研究。在他看来,新诗最大的问题在于诗人们误认为诗歌应该抛弃一切形式的束缚,仅依赖“语言的精选与安排”来创作,但实际上,新诗的停滞不前正因为它缺乏形式上的标准。为了进一步推动新诗的试验,沈从文在其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和《益世报·文学周刊》上坚持刊登新诗,鼓励多方人士参与讨论和研究。即使在诗歌备受冷落的时期,他本人对诗歌的创作热情也从未减少。
依据诗歌的语言体例,沈从文的诗歌主要有三类:土话诗、白话诗和旧体诗。前两类构成了沈从文在新诗方面的建树,1961年后,他则转向旧体诗的写作,力图以“诗”写“史”,以“诗”为“学”。在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沈从文诗集》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沈从文在诗歌领域贯穿一生的不懈探索。全书共分六辑,涵盖新诗及旧体诗73首,这些诗作大多收录于他的第一部作品《鸭子》中,也有不少散见于当时的各大诗歌杂志和报刊,但从未单独以诗选的形式集结出版。如今再次“出土”,这本诗集或许可以为沈从文的诗人身份提供更加充分的阐释。
将沈从文的新诗与小说、散文对照阅读就会发现,它们之间有明显的的互文现象。譬如,诗集中的第一辑《镇筸的歌》为沈从文采用家乡凤凰土语所作的诗歌,他将民间男女对歌的形式借鉴到诗歌的写作中,字里行间流露出浓郁的湘西风情;在《忧郁的欣赏》、《絮絮》、《浮雕》三辑中,他借由诗歌纾解爱欲、感喟时事,诗篇《爱》《颂》《曙》《絮絮》都是这方面的佳作。这些诗歌呈现了与沈从文其他作品中一致的美学,在人们熟知的《凤子》《边城》等小说中,读者也可以找到它们的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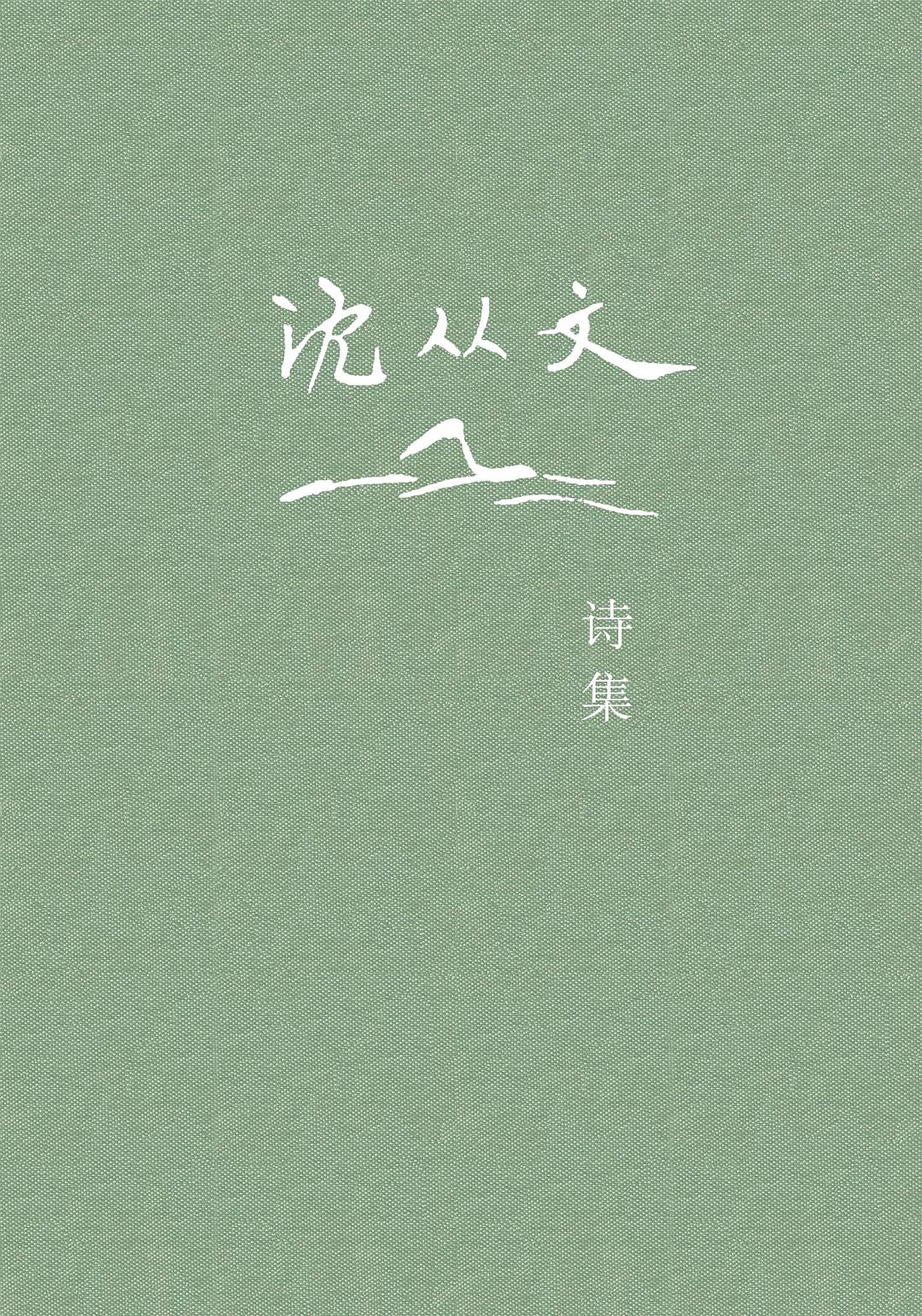
沈从文 著 张新颖 编选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07
初恋
到阎王殿去抽陀螺,
这意思我不说妈同爹都不知道。
抽,抽,抽,抽,
陀螺在地上转成一团风了;
还是抽,抽,抽,抽。

我身子好像也慢慢转起来,
我身子好像也慢慢转起来;——
似乎也变成一个陀螺了!
因为庙里那个年青青底尼姑,
一对亮晃晃底眼睛,
同我手中这条小鞭子一样。
“师父嗳,师父嗳,
你莫要抽了吧!
你再抽我,我回家去就会大哭!”
师父莫有听我的话,
我脸庞儿绯红偷悄悄跑回家,
师父的鞭子我实在怕!
我梦里常常变成一个陀螺,
是敷有金赤美丽颜色的精致陀螺,
在年青的师父鞭子下最活泼的旋转,
在年青的师父手上卧着歇憩:
师父底梦我不知,
但是,我一到阎王殿,
师父的鞭子就在我身上抽来抽去。
一个夏天的时光都消磨到阎王殿那片三合土
的坪上了,
别人说我爱抽陀螺成了癖。
这意思我不说爹妈都不知道:
我是跑去到那里让年青的师父用鞭子抽我底。
十四年七月,于北京。
(本篇发表于1925年9月20日《京报·国语周刊》第15期,署名沈从文。)
黄昏
我不问乌巢河有多少长,
我不问萤火虫有多少光:
你要去你莫骑流星去,
你有热你永远是太阳。
你莫问我将向那儿飞,
天上的岩鹰鸦雀都各有巢归。
既是太阳到时候也应回山后,
你只问月亮“明后里你来不来?”
(此篇发表于1932年4月30日《文艺月刊》3卷4号,署名芸芸。后又写入小说《日与夜》(《凤子》的第九章,载1932年6月30日《文艺月刊》第3卷第5—6期)中,个别用词略作改动。)
残冬
横巷的这头,
横巷的那头,
徒弟们的手指解了冻,
小铺子里飏出之面杖声已不像昨日般生涩了。
朋友们中有人讨论到袷衫料子,
大路上的行人,已不复肩缩如惊后之刺猪,
街头屋角,留着既污之余雪。
电线上挂了些小小无所归的风筝,
孩子的心又挂在风筝上面。
轻薄的杨柳,
做着新梦——
梦到又穿起一身淡黄裙裳,
嫁与东风!
比梦还渺茫无凭据的,
是别处飞来的消息!
我的心,西伯利亚荒寒之一角,
长出了,一对青青的小小的嫩叶。
十五年元日
(本篇发表于1926年3月13日《晨报副刊》第1362号,署名小兵。后收入1926年11月上海北新书局初版的《鸭子》集中。)
爱
自从我落地后能哭能喊之时,
把骄傲就一齐当给了你!
用谦卑的颜色在世上活着,
我不是为饼也不是为衣。
我跋涉过无数山河足生了胝,
大漠的风霜使我面目黧黑:
你呀,先要我向那些同类追随,
如今是又要我赶逐那些婴儿!
一切事一切事我都已疲倦了,
请退还我当给你那点骄傲:——
我将碰碎我的灵魂于浪女吻抱!
我将拍卖我的骄傲供我醉饱!
我将用诅咒代替了我的谦卑,
诅咒中世界一切皆成丑老!
我将披发赤足而狂歌,
放棹乎沅湘觅纫佩之香草!
三月七日 西山
(本篇发表于1926年3月18日《晨报副刊》第1365号,署名茹。)
想
像撒盐,像撒面,
山坡全是戴了白帽子。
请你吃那当时的东西,——
手笼灰中煨熟的干板栗!
雪中猎狐、猎兔、打野猪,
不能看,就蹲在灶边去跟人学吧。
陪猫儿据炉边烤火,
你也困,我也困!
跌下去,就莫起来了,
横顺要作雪罗汉!
不要唱歌,不要吹笛,
山谷已经不愿再作回声了,
雪把它封了口。
长的河坝胖了,
老的碾房胖了,
水磨学得胖子的脾气,
唱歌也只是懒声懒气的!
日头从云里出来时节,
喊着叫着的斑鸠,
是坐在我家正屋背脊上。
人穿了草鞋,
牛穿了草鞋——
到官路上去吧,
可以看烂雪里各式各样的脚迹!
(本篇发表于1928年4月10日《小说月报》第19卷第4号,署名甲辰。)
颂
说是总有那么一天,
你的身体成了我极熟的地方,
那转弯抹角,那小阜平冈;
一草一木我全都知道清清楚楚,
虽在黑暗里我也不至于迷途。
如今这一天居然来了。
我嗅惯着了你身上的香味,
如同吃惯了樱桃的竹雀;
辨得出樱桃香味。
樱桃与桑葚以及地莓味道的不同,
虽然这竹雀并不曾吃过
桑葚与地莓也明白的。
你是一株柳;
有风时是动,无风时是动:
但在大风摇你撼你一阵过后,
你再也不能动了。
我思量永远是风,是你的风。
于北京之窄而霉斋中
(本篇发表于1928年11月10日《新月》第1卷9号,署名甲辰。后收入1931年9月新月书店初版的《新月诗选》。)
对话
你说“我请你看你自己脚下的草,
如今已经绿到什么样子!
你明白了那个,
也会明白我为什么那么成天做诗。”
“你说水不会在青天沉默的,
它一定要响;
鸟不会在青天沉默的,
它一定要唱;
你为什么自己默默的,
要我也默默的?”
“可是,你说的那草,
它也是默默的。”
(本篇发表于1931年9月新月书店初版的《新月诗选》,署名沈从文。)
本文诗歌部分选自《沈从文诗集》一书,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