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 | 董子琪
编辑 | 黄月
他们的人生故事,充满着绝处逢生的传奇感。莫砺锋来南京大学读研究生之前对中文系毫无概念,只在农村背过几千首唐诗宋词,更不认识日后的导师;葛剑雄在进入复旦大学之前,并不知道自己将要读的专业历史地理是做什么的,只觉得历史和地理都是喜欢的学科;李伯重没有读过本科,也没有参加高考,在父亲的鼓励下直接考取了厦门大学中国经济史方向的研究生。他们都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批文科博士。
新中国的博士培养制度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已有近40年的历史。近日,《开山大师兄: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访谈录》一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了十位不同学科的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的访谈。他们基本上都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开始本科或者研究生学习的一代学人,其中就包括第一位中国古代文学博士莫砺锋、第一位历史地理学博士葛剑雄、第一位中国古代史博士李伯重。
“他们这一代学者,在从事学术生涯之前,有的做过工人,有的做过农民,他们深深地跟中国社会和土地紧密相连的,这种相连性一方面赋予他们家国情怀和时代感,另一方面也让他们的研究具有温度和厚度。”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采访时,访谈录编录者之一许金晶如此说。许金晶提到,此前对这些教授以博士求学生涯角度切入的访谈和资料是很少的,他希望通过这本书反映出这批学者在博士阶段的训练和研究,以及他们在博士之后的学术生涯跟整个国家、时代变迁之间的动态关联。所以,借由这批学者对于个人博士生涯的回顾,我们不仅可以了解他们在80年代的求学之路、治学之道,也可以窥见新中国文科各个学科的发展历程。
需要注意的是,书名中的“大师兄”一词并不能概括新中国第一批的所有文科博士,因为这批人中不仅有“师兄”,也有“师姐”,比如第一位国际法博士梅小侃(1986,北京大学)和第一位政治经济学博士赵涛(1985,中国人民大学)。对此许金晶说,书名来源于公众号“群学书院”推送的一篇文章《开山大师兄》——这篇文章列举了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的名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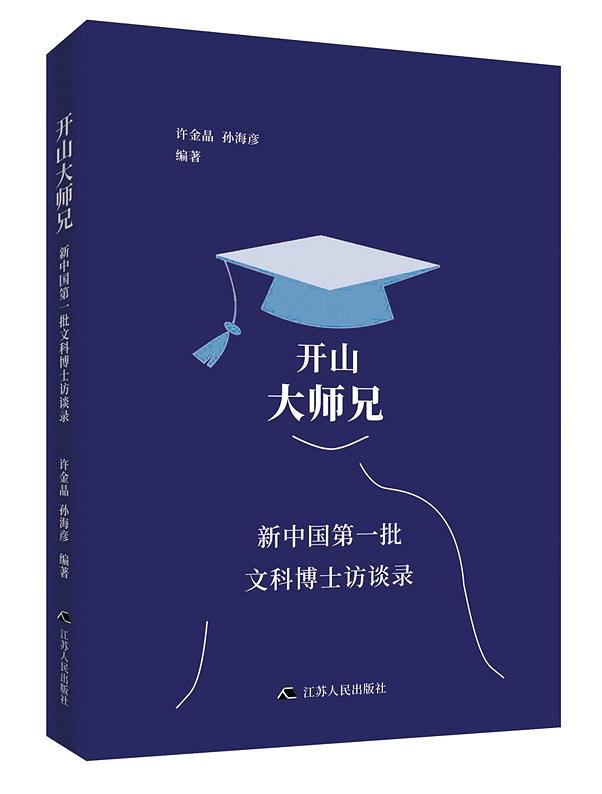
许金晶 孙海彦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9年1月
成为博士之前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陈洪捷在书中序写道,虽然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的人生故事各有不同,但是他们在学术方面都有着相似之处,比如“基础不好”、“缺乏系统的训练”、“甚至中学和大学的教育都不完整”。在本书新书首发沙龙中,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莫砺锋也感慨道,“我们这些‘开山大师兄’的学术水平远远逊于我们的先辈导师们,基本上可以断定,我们这一辈人中是出不了大师的,因为我们的教育过程是断断续续的、不完整的,所学也非本人所长。”
在《开山大师兄: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访谈录》中,不少学者都回顾起了当年“无书可读”的窘迫和遗憾。莫砺锋回顾道,当年离开中学下乡时,他曾从图书馆里“拿”了二三十本书,但是这些书很快就看完了;至于那些北京城里的孩子可以看到的书,比如“文革”期间非公开出版的黄皮书和白皮书,他是进入大学之后才接触到的——读书零零星星、缺少系统,也影响了日后的知识构成。他说,“假如那十年有一个图书馆供我用,也许我现在会比较有学问……我自己的知识构成,都是零零星星的材料拼起来的。”
清华中文系教授罗钢也讲道,自己在“文革”期间能够读的书极其有限,除了《马恩列斯全集》《毛泽东选集》《鲁迅全集》几乎无书可读——“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外国文学都成了‘封资修’”,罗钢说,也正是因为那时候所读的书极其有限,所以有些学者比如钱理群和王富仁对于鲁迅有着深切的感情。“真是全心全意地反复地读,因此而形成的理解和感情是后人不能想象的。”幸运的是,他某个朋友的父亲在省图书馆的书库工作,所以他可以每周去借书还书,只是这种做法也并不是万无一失的;有一次,他的“黄色小说”《欧也妮·葛朗台》被工宣队的师傅没收了,为了要回这本书,他还写了一个“沉痛深刻”的检查在全体同学面前宣读。
复旦大学资深教授葛剑雄则提到,深厚的社会实践经验对人文社科的研究是有益处的。“文革”期间,他曾在中学专管坏学生,那时候停课了,学生干什么的都有,打架斗殴也不稀奇;他还被派到公检法上班,不仅审学生,还跟着把犯人押解到外地。“一个人真正要了解社会,一定要做研究,实际经验是非常重要的。”葛剑雄说,之所以后来进入大学之后能做导师的助手,又做图书馆馆长,不仅是因为学术能力强,还因为他可以处理许多“复杂的问题”。“我什么人都见过,流氓、女人拍手跺脚在我面前打滚我都能对付,学生在我面前拿一把刀出来对我都是小事。”

“老艺人培养学徒”的方式
在他们作为新中国的第一批研究生进入高校之时,中国的研究生培养制度还远未完善。罗钢在访谈中讲道,那时的第一批研究生受的约束比较少,不像现在的学生要经历开题报告、中期报告多个步骤。当时他问自己的博士副导师童庆炳论文应该怎么写,童庆炳从书架中抽出了一本厚厚的书说,“写到这个样子就可以了。”那本书也是第一批文学博士的论文——王富仁的《<呐喊><彷徨>综论》,长达50万字。
莫砺锋回忆,那时研究生上课既没有课程,也没有学分,几乎全靠导师一对一的指导。他的导师程千帆当时只有他一个学生,他的学习方式就是经常去导师的家中与导师聊天。然而就是这种“聊天”启发了他日后的教学,莫砺锋说,“要说我对我的学生们有什么帮助的话,主要不是我开的那些课,而是每两周一次的聊天讨论。你读书时遇到什么疑难,你拿来向老师请教,老师帮助你一起思考。特别是对于文学研究领域而言,文学研究者应该有学术个性,不是千人一面。所以最好的师生传授模式就是一对一,有点像从前社会上老艺人培养学徒。”

莫砺锋所说的“老艺人和学徒”的故事不是孤例,现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的马敏也在访谈中提到,他每周都要去导师家里喝茶聊天,在聊天中,同学们会彼此交流——比如他会分享自己研究早期资产阶级构成的心得,他的同学桑兵则会讲对于辛亥革命时期学生团体的发现,导师也会在此时补充一些学生们需要阅读的材料。所以虽然那时学校没开设什么课程,但他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了学术指导。
学生与导师一对一的传授方式在葛剑雄的故事中也有体现。他在学校待的时间并不久,平时是上完课就回家;做了导师的学生之后,就开始导师家、学校和自己家三个方向轮流跑。他说自己和导师谭其骧的交往不仅仅是学术上的,也有生活上的。比如编《中国历史大辞典》的时候,他与导师一同在申江饭店长达9个月,这期间,他不仅要帮助导师找文献材料,还帮助他处理学术和行政事宜,中午一起散步聊天,交流学术观点,导师也会跟他讨论“正在形成的观点”。通过长时间的接触,葛剑雄甚至可以比导师的家人还要了解他的思想和为人。“在这个过程中,他本身的所作所为,他的言行,给我树了榜样……”
对今日学院的反思
三十多年后,第一批博士生终于成为了教授和导师,学院与学术机制也已经变化,他们对此又是如何看待的呢?“作为七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学者,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怀旧情绪,觉得现在学术与各种经济利益挂钩,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排斥。”许金晶对界面文化说。今昔对比,高校学院注重量化考核、学术风气有待改进,也是第一批文科博士在访谈中提到的话题之一。
罗钢在访谈中说,近十年学术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是权力和金钱的侵蚀,”他们当年写文著书是没有直接利益的驱动的,给最好的刊物发文章,“贴一张八分钱的邮票就寄过去”,现在指导博士生发文章,结果对方要一万五千元的赞助费;“二是量化考核,规定每个教师每年要发表多少文章,”再根据考核结果来发薪水。还好这种“量化考核”受到了清华大学人文社科教师的抵抗,所以清华也是全国高校人文学科里坚持到最后都不搞量化的。“这些人如果是真正的学者,你不让他思考他也一定会去思考,你不让他写作他也一定会去写作,但是不要跟他说今年要怎么样,明年要怎么样,给他强加很多束缚。”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伯重也在访谈中谈到了中国学术生产中的问题,“现在中国学术风气不良,是很明显的。我十多年前写了一篇文章,就说道中国学术风气不好,许多大学学报成了学术垃圾生产地。”
他们注意到,近些年,不仅学院与学术风气与往日不同,学生也在发生着变化。李伯重说,现在有些学生读研究生是为了将来做公务员,但他更希望自己的学生是有志于学术的,所以就会跟这样的学生谈话,建议他们换导师。罗钢则讲道,他的一位师兄讲鲁迅小说讲得很投入,然而在汕头大学讲课时却被学生提问:“老师你讲这些有什么用呢?”师生之间没有共鸣,学生无法理解文学之美,这对老师来说,也是“兜头一盆凉水”。
……………………
| ᐕ)⁾⁾ 更多精彩内容与互动分享,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和界面文化新浪微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