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先生,我们好像又开始在聊天了,在我的耳边仿佛又听到你那轻轻的、柔柔的带着南方口音的声音。现在的你一定很轻松,耳朵不背了,可以听见我说话了吧?
我和先生一定是有缘的。当时我们都在社科院外文所,她是大专家,我是《世界文学》编辑部的一个小编辑。“文革”中“革命群众”贴大字报揭发钱锺书的书桌上从来不肯放毛主席的书,杨先生知道了就连夜打着手电,在大字报旁贴了一张小字报,说这不是事实,这件事激怒了“革命群众”,然后批斗了她一次。另外在外文所一次小型的批斗会中,“革命群众”让学术权威们每人脖子上挂了一个黑帮牌子,手里拿一个盆或者锣,一边敲着游街一边说自己有罪。在这次批斗会中,杨先生真让我敬佩。她最瘦小,但把锣敲得最响、最愤怒,当时觉得这么一个瘦小的老太太胆真大,内心居然这么强大!后来她被惩罚去打扫女厕所,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中对此有所回忆:“有一个平时也并不很熟的年轻人对我做了个富有同情的鬼脸,我不禁和她相视而笑了。时过境迁,群众有时还谈起我收拾厕所的故事。可是我忘不了的,是那许多人的关心和慰问,尤其那个可爱的鬼脸。”杨先生后来告诉我那个年轻人就是我,我却一点都不记得了。我当时还算是“革命群众”,比较自由,但仍是黑帮子女,对她做个同情的鬼脸完全发自内心。
20世纪70年代我们都下放到五七干校,她在菜园子劳动,我随大队一起下地干农活,都在改造中。所以和杨先生接触得稍微多一点,钱锺书先生当通信员,每天上邮电局取报取信,有空就顺便过来看看杨先生,和她一起散散步、聊聊天,这也是他们最浪漫的一刻。有时见到我们打个招呼,有时还给我们(我和刘慧琴,她是我的好友,也是杨先生的忘年交)带一点当时吃不到的零食。一次,钱先生给我们一个罐头食品,他认为不太好吃,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吧!”至今我还记得他的幽默。
1971年干校由宿县整个搬到明港,几十个人同住一间大宿舍,我们接触更多了。再后来老弱病残陆续调回北京,钱先生和杨先生第二批一起走,大家都为他们高兴。那时是3月份,虽然已是春天,但屋子里还生着火,我和刘慧琴就琢磨怎么做点好吃的给杨先生饯行,于是决定到外面去挖野荠菜,包一顿荠菜肉馄饨给她吃,又剁肉又洗菜,忙活了半天,才发现馄饨馅调得味道太淡,不好吃。为此事我后来一直懊恼,没想到杨先生还记得,写到《干校六记》里去了。
干校回京,他们在干面胡同旧居没住多久,就因“掺沙子”进来同住的那位强势造反派实在难处,被迫“逃亡”,避居到钱瑗在北师大的一间狭小的宿舍,后来又搬到学部七号楼底层的一间办公室居住。那间屋里堆满了杂物,多年没有打扫,脏得很。好在有大家(那些被杨先生称为“披着狼皮的羊”的年轻人)帮忙收拾,很快就弄干净了。他们总算有个地方可以安顿了。房间里只搁了两张折叠床,两张床中间放一个木箱,充当床头柜,另加一张桌子和一个箱子。那屋子正如杨先生所说的,“吃喝拉撒全在此了!”房间靠窗的走廊很深,屋内光线暗淡,钱先生灰尘过敏,一不小心就要犯哮喘,窗缝被封得实实的,空气流通又不好,这可真难为他们了!好在这时钱瑗也在北京,常来看看他们,三个人总可以干自己的事情了:钱先生在写《管锥编》,杨先生在译《堂吉诃德》,钱瑗在学校工作。他们三人只要能聚在一起,再困难也感到幸福。在这间简陋的办公室里他们熬了四年,才搬到三里河比较宽敞的单元房。钱瑗在那儿也有了自己的房间,他们仨才真的团圆了。他们多次说:“我们总算有了自己的家了。”三里河寓所真是他们晚年的安乐窝了!

我说我和杨先生有缘,其实他们和我父亲夏衍虽然来往不多,但相互钦佩,相互关怀。我曾多次听父亲对我说,钱锺书是个大学者、活字典,他“中外古今一脚踢”。有一次在一个文艺座谈会上李健吾老先生大捧钱先生,我父亲就说,“你们捧锺书,我捧杨绛”,因为父亲原来写过剧本,他品得出杨先生的剧本写得好。整理父亲遗物时,我发现他在一个小笔记本上,抄录有杨先生文章里的一段话:

人物的对话,口气里可以听出身份,语言里可以揣想性格,但人物的状貌服饰,本人不便报道……若用对话,则需从别人口中道出,这也得按各人的身份,找适当的场合。(——杨绛《旧书新解》,《文学评论》81年4期)
1994年我父亲生病住北京医院,一天,我在三楼走廊里遇到了杨先生。她手上提着暖壶,扶着墙艰难地一步步走着,原来她要去打开水,我才知道钱先生也在住院。回来把这消息告诉了父亲,他马上说,那不行,得照顾他们。父亲通过官方渠道,通知了有关部门,使钱先生的就医条件得到了改善,并找到了一个好的护工。那时我每天中午给父亲送家里做的菜,常常顺便先到三楼也给他们送一份,他们是南方人,吃得惯我们家的南方菜。
后来钱先生因牙床萎缩,不能装假牙,进食只能通过鼻饲。医院里鼻饲的食材都是冷冻的,不太新鲜,杨先生于是决定自己做。我替他们找了一个很小的粉碎机(当时不太好买)。可以把鸡鸭鱼肉等食材打碎,让先生吃下去,增加点营养。这就忙坏了杨先生,每天把有营养的菜换着花样做好、打碎,送到医院。这样虽然辛苦,但杨先生没有任何抱怨,我想她为钱先生做任何事都会觉得是幸福的。当时她对钱先生的病情也是充满乐观的。
1998年12月19日清晨钱先生去世,杨先生找到我,说按钱先生遗嘱,死后马上火化,不留骨灰,不搞仪式,她希望最好第二天就火化。我听了大吃一惊,觉得这么大个人物,怎么也得开个追悼会隆重悼念一下。我说不要骨灰,那就和那些不要骨灰的老百姓撮到一块去了?杨先生说,钱先生就是要这样。她希望马上火化,最好明天,让我给想办法。但第二天是星期日,那时北京只有八宝山一个火葬场,一般高级干部火化都得等个十天半个月。尽管知道很难,我还是答应去想想办法。因为1995年我父亲和我丈夫相继去世,八宝山火葬场,我倒是有几个熟人。第二天我去找了火葬场管事的同志。八宝山火葬场的工作人员送走的大人物多了去了,但听说要马上火化,他们还是第一次遇到,都很诧异。我求他们说:这是一位大作家,也是一位大人物,他不要搞仪式,也不要租礼堂,一切从简,死者就这么一点小小的要求,你们就帮帮忙吧。他们中也有知道钱先生的,就破例定于星期一上午举行火化!据旁人统计,说钱先生从去世到火化只等了50多个小时,这在当时算神速了。
火化那天,没来多少人,也没有满屋子的花圈。只有社科院党委书记王忍之来了,他们的无锡老乡李慎之大病后也扶着拐杖来了。机关的同事来得并不多,新闻记者更少,现场比较清静。那天天很冷,杨先生给钱先生穿了一套中山装,里面穿的是女儿给他织的厚毛衣毛裤,外面穿上大衣,戴一顶他常戴的贝雷帽,身上盖了一条白色的单子。我连夜用白色和紫色的花编了一个小小的花盘,经杨先生同意,放在他身上。同时也照我父亲火化时那样,在遗体上洒满红玫瑰花瓣和白菊花瓣,让先生在花丛中安详地走完最后一程!遗体往火化炉推时,同事薛鸿时从工人手中把车接过来,推着钱先生,说:“我也最后送先生一程。”杨先生一身黑衣,沉重地一步一步跟随遗体走到火化炉旁,直到把钱先生推进火化炉,杨先生要目送钱先生走。火化时间不长,因为关照过,火炉风门要开得很大,骨灰少,时间短,杨先生一直站着,虽然她当时身体不太好,但她坚持着没有流泪,没有倒下,内心的痛苦也只有她知道。

杨先生最伤心的事,莫过于钱瑗的走。那么优秀、那么阳光的女孩,那么好的老师,那么孝顺的女儿,怎么就先他俩而走了呢?按杨先生的说法,去世“应是男在前,女在后”,白发人送黑发人是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我和钱瑗接触不多,只知道她特别忙,天天背个大书包挤公共汽车去上班。一天杨先生说,阿瑗病了,住院了,可能是扭了腰。一开始杨先生大约真不知道阿瑗得的是什么病,她只知道她的腰有过伤。其实钱瑗是癌症扩散,但当时大家都瞒着她。我也觉得奇怪,怎么扭了腰会住到远郊的胸科医院去呢?她们母女天天通电话,相互安慰。渐渐地杨先生有些不安了,打听出了阿瑗病情的真相。她一面要瞒着阿瑗的病情照顾钱先生,一面还要去远郊的胸科医院看阿瑗。
1997年3月初的一天早上,杨先生给我打电话,口气很急,叫我去她家。我不知什么事,去晚了一些,她接着又打了个电话,语气更显着急了。我一到,她就直接带我到钱瑗的屋里打开她的箱子,叫我帮忙挑选衣服,要钱瑗喜欢的又能搭配的衣服。杨先生虽然没说什么,但我心里知道,一定是接到病危通知书了。真是欲哭无泪呀!后来杨先生告诉我,钱瑗去世那天她坐在床边,钱瑗没有痛苦,安详地握着妈妈的手说:“妈,我想睡觉了!”就这样安静地走了。钱瑗也是不要留骨灰,但舍不得她的学生们,还是偷偷地把她的骨灰埋在一棵她经常走过的大雪松树下,让她入土为安!
送走了女儿和丈夫,杨先生独自一人回到了三里河的家。她需要用多大的毅力才能把心头的痛压下去!过了不久,她慢慢克服了精神上的创伤,开始整理钱先生的书稿。她把钱瑗住的房间改成了一间书房,做了一整面墙的书架。她告诉我,她天天在这儿工作。
三里河的房子,当时是所谓的高级单元房。入住时阳台是没有封的,后来公家出资为各家封阳台,每家都愿意封,独有杨先生家不封,她说要留一片天空,可以天天往外看看。这样她才看见了窗外老树上那对老喜鹊失去小喜鹊的痛苦,触景生情写下了《记比邻双鹊》那篇感人的散文。
杨先生一生勤奋写作,数量多且品种多。她外语基础好,但从47岁上开始学西班牙语,并翻译塞万提斯的巨作《堂吉诃德》,堪称奇迹,快九十岁时又翻译了柏拉图的《斐多》,更令人意外。
她也是一位奇女子!说她“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一点不为过。年轻时在国外有一次她把钥匙忘在房里进不了门,居然能翻窗进屋。钱先生吃不惯西餐,她会想着法就地取材,做出钱先生爱吃的饭菜。在上海沦陷期间,她辞去了用人,从斯文的千金小姐变成了家庭主妇,既挎篮子上街买菜又生煤球炉。她不但会做饭,会做衣服,还能爬上凳子修电灯,会用推子给钱先生理发。当然她也命大。虽然在干校几次迷路,差点掉到粪坑里淹死,回北京暂住办公室时,差点煤气中毒,但她都化险为夷了。她生活窍门也多,曾有一次她兴冲冲地告诉我,蜜饯放时间长了、干了,只要用少许红酒泡一泡,就能“还魂”。她是一个有生活情趣的人!
其实杨先生身体并不太好,先是嗅觉坏了,闻不出味道,她说食物馊了她也吃不出来,得告诉她。后来耳朵逐渐失聪,年老体衰、失眠,还经常感冒……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她能坚持自我保健,做八段锦,天天吃黑木耳,饭后吃一些开心果……这是因为她心态好,一定要把该做的事做完,让那颗受过伤,但也十分坚强的心静下来、静下来,一百多岁还在写作,并且还打了一场官司!

有一事,至今让我不解。“文革”期间,一位“革命群众”抄家时,把他们家一尊鎏金的佛坐像,狠狠地按成了90度角,让这尊佛也低头认罪,永世不得翻身!这尊佛像身体是鎏金的、空心的,比较软,但头却是铸造的。杨先生曾多次说过这尊佛像的脸是最美的。佛像被压弯以后,杨先生只好把它藏起来,她觉得总不能放在外面让佛老对大家低头吧!后来我们提出说想办法找人去修修看。但因为是佛,又不能随便让不了解的人修。正好我弟弟手巧,就交给他修理。他努力修了,但佛的身体还不能完全伸直,他怕再用力佛头会掉下来。后来我找到上海博物馆的专家,好容易才修复到身体差不多能直起来。这尊佛前前后后在我家起码放了三四年,杨先生从来没问起过,可等刚刚修好送回北京,她第二天就来了电话,问佛像修好了没有,她想看看。当时我真是惊呆了!心想我又没告诉她,她怎么会知道佛像回来了?是佛先告诉了她,还是她心有灵犀呢?第二天我和女儿拿去给她看,她见了大喜,立即搂在怀里,高兴极了!
最让人钦佩的是,“文革”期间,在干面胡同住的时候,被那“左派大娘”恶毒地给她剃了阴阳头,当时钱先生急得不得了,怎么办?第二天怎么出去?杨先生临危不惧,不慌不忙,找出了先生以前用过的压发帽,钱瑗剪辫子留下的头发,连夜做了一顶假发,猛一看,还真看不出来!
杨先生,我常常在想念你,但我能回忆起来的却只是一些零碎片段,这些碎片太多,而且我也写不完。
杨先生!我一直觉得你不是一个凡人,你身上有仙气,你完成了你在人间的一切任务后才走。你说,怕你老成这样,地下的亲人们会不认识你。其实你不用怕,他们都在等着你呢!你们仨相聚在天堂,一定会永远幸福!
2016年8月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文学》编辑。本文选摘自《杨绛:永远的女先生》一书,较原文有删节,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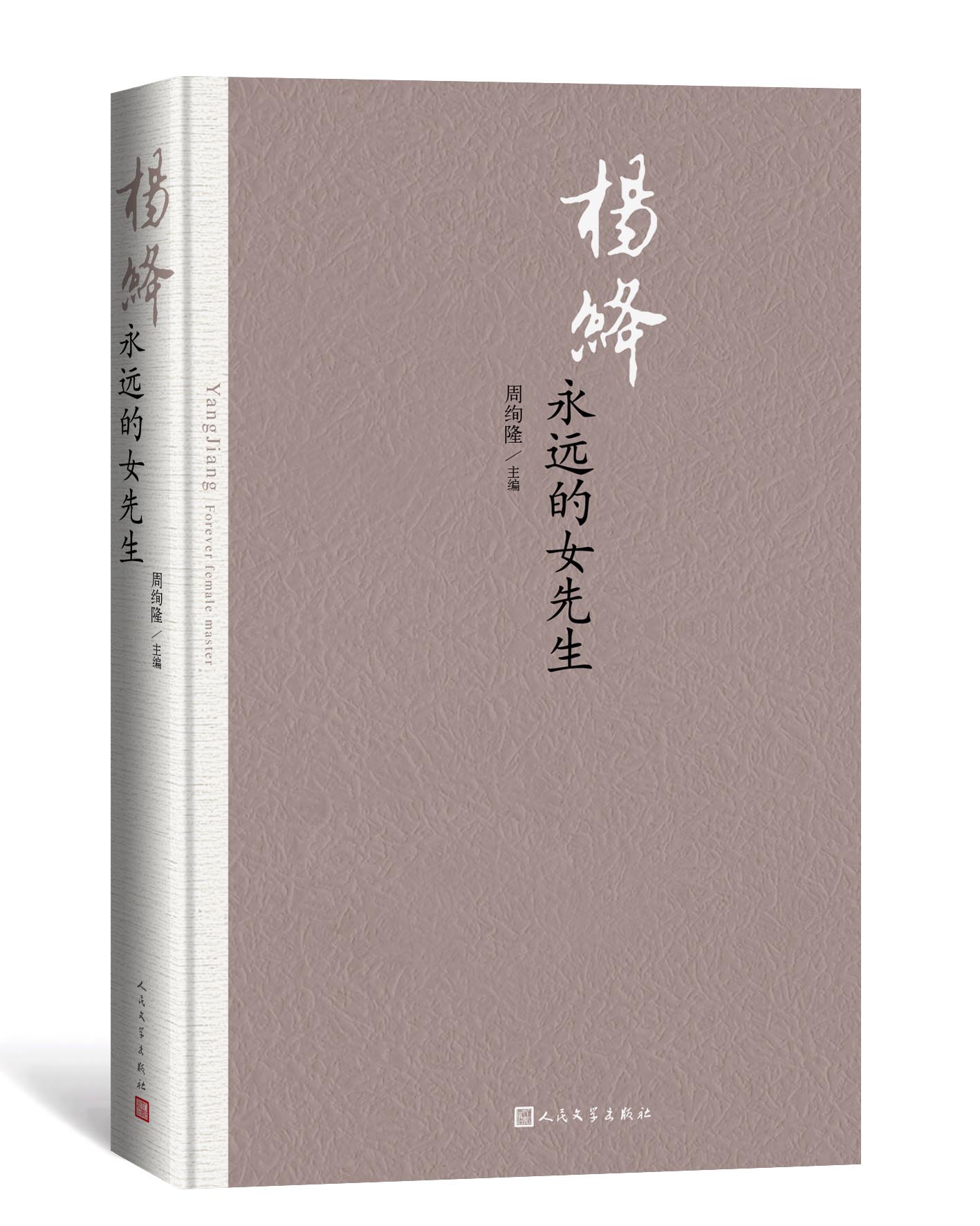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12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