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底层”?
是一个社会中收入最低的人群?是缺少尊严和成就的人?是又懒又笨被社会抛弃的人?是无法改变命运的人?还是失去声音和权利的人?
他们(或者我们)为何是“底层”?
是遗传的卑贱,还是教育的失败?是懒惰的恶果,还是分配的不均?是制度所生,还是意外所致?
今天,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希望通过三本书,走近三个时代三个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三种所谓“底层”。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穿过空间与时间的区隔,面对着相似的贫穷、失声与无助。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威根码头之路》探访了生活于“地狱”之中的矿工,他写道:“建立在矿产之上的社会,最终会忘记矿工的存在。”美国作家芭芭拉·艾伦瑞克放弃身份,扮作女佣、女侍和超市店员历尽辛酸,她在《我在底层的生活》一书中说:“他们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获取微不足道的收入,而人们根本看不见他们。 ”中国记者袁凌的《青苔不会消失》聚焦于中国村庄里劫后余生、沉默不语的人们,“他们仍然只是生活剧场灰色的布景,是没有机会购票入场的主角”。
当我们谈论底层的艰辛与社会的不公,我们究竟在谈些什么?

他们是不知脏臭的天生贱民吗?
时间 | 1930s
地点 | 英国威根码头
记录者 | 乔治·奥威尔
记录对象 | “地狱”中的矿工

“这里就是一片地狱。”
上世纪30年代,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乘坐火车前往威根码头——一个矿渣堆积如同月球环形山的丑陋工业区——探访矿工们的生活和工作状况。他进入矿井,发现了一片人间地狱,这里有着地狱的一切要素——燥热、噪音、混沌、黑暗,污浊的空气和难以忍受的逼仄空间,矿工只能头戴安全灯、手拿手电筒通过,唯独缺了“地狱烈火”而已。
矿工超负荷工作,他们跪在“地狱”之中,以每小时以接近两吨的速度挖煤;他们一天上班七个半小时,这并不包括一小时或者更长的走矿时间,理论上没有任何休息时间,只有十五分钟吃掉随身携带的黄油和面包;他们每呼吸一次,就吞入一把煤尘,煤尘渗透进身体每一处伤口,皮肤愈合便形成一个个蓝色的痕迹,当他们结束一天劳作从矿井中爬出,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鼻子和额头上的蓝色伤疤,“有的男人额头上纵横交错,就像罗克福羊乳干酪一样”。相较于随时丧命于瓦斯爆炸的危险,这些蓝色印记或许根本不值一提,此外,他们还面临着肺病、风湿和眼球震颤等等疾病及残废风险。
奥威尔计算,一个普通矿工如果工作三十年,可以产出八千四百万吨煤。付出如此巨大的劳动量,矿工们却只能领取与劳动量完全不相符的微薄报酬。挖煤按吨算钱,如果机器出了差错,比如煤层里混入岩石,几天的工作便白费了。矿工们能支付得起租金的房子多集中在臭烘烘的铸造厂和恶臭难当的运河旁边,房龄通常长达五六十年,七八个人挤在屋顶漏雨、蚊虫侵扰的环境当中,女人浑浑噩噩地干着苦差事,却永远无法让家中保持干净。“这样的环境没有尊严,”奥威尔认为,矿工们的绝望只有在他“浑身涂满大便时才能比拟”。
他们天生是贱民吗?他们对于贫困和肮脏无知无觉吗?
奥威尔在经过一间贫民房时,见到了一个女人。她正在后院用棍子捅排污管,她有着一张常见的、疲惫的苍白面庞,却带着他平生见过的最为凄惨绝望的神情。奥威尔意识到,她此刻的所思所想,一定和他自己的一模一样:“说生长于贫民窟的人除了贫民窟以外想象不出别的东西,是不对的。因为我在她脸上看到的,不是动物那种懵懂的受苦。她非常清楚自己身上在发生什么——她和我一样明白,天寒地冻之中,跪在贫民窟后院黏滑的石头上,往肮脏的排污管理捅棍子是多么残酷的命运。”他将这一经历和想法记入日记,又将之扩充写入了《通往威根码头之路》一书。
“下等人臭”、“工人阶级更臭”是奥威尔从小被教予的信条,奥威尔在之后的篇章中提起,认为这是人们在理解所谓底层时无法逾越的障碍,因为无论如何,人类所有的喜恶都建立于生理感觉之上。“你可以对杀人犯或者鸡奸犯产生感情,但你没法对口臭的人产生感情。”与认为无产阶级懒惰、酗酒、粗鲁或不可靠相比起来,认为他们“脏”和“臭”才更要命。
矿工们是否真的臭气熏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并非他们的选择。“他们并没有自主地选择脏”,奥威尔说,那只是因为他们工作和生活在“地狱”之中。
他们是懒惰者与堕落者吗?
时间 | 1990s
地点 | 美国某州餐馆及超市
记录者 | 芭芭拉·艾伦瑞克
记录对象 | 女佣女侍等底层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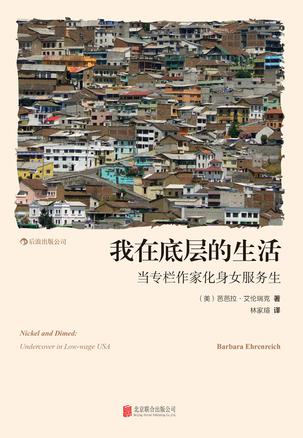
美国作家芭芭拉·艾伦瑞克在五十年后对于底层的深入体验,如同奥威尔探访矿工生活的一次遥远回音。芭芭拉出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美国矿工家庭(正好与奥威尔访问威根码头的时间相近),凭借自己努力获得博士学位,并成为了一位专栏作家。
在五十岁时,她暂时放弃了自己的身份,假扮成一位刚刚离异的单亲母亲,先后在美国佛罗里达的餐馆、缅因州的和明尼苏达的沃尔玛超市充当女侍、女佣和店员,经过了数次羞辱(包括药物验尿等),被男人们喊做“蜜糖”、“宝贝”或“金发妞”。
餐馆女侍,时薪2.43美元,一天八小时周转于摆台送菜、擦抹桌子与备货之间,客人像浪潮一样冲来,“几乎没有人能够撑完第一天第二天还回来”。缅因州的女佣工作比女侍更加艰苦屈辱,她背负着14镑重的吸尘器,在挑剔的女主人的指挥下,以匍匐在地的“原始服从姿势”清扫灰尘,而重复操劳造成的关节炎和肌肉疼痛只能靠止痛片来缓解。在沃尔玛超市做店员,她每天收拾折叠着被客人扔乱的衣服,再分类挂回到原先的位置上,无穷无尽。
换过几种低薪工作,女作家芭芭拉的底层身份从未受到怀疑。她发现,低薪工作不仅使生活难以为继,仅仅是拿到超低工资受到的贬损,就“会使你觉得自己如同贱民”,“时间不值钱”,“脑子很笨”,“有不良的生活习惯”,她第一次明白了“身为黑人是什么感觉”。
身为女佣、女侍和店员,芭芭拉不仅要面对顾客的种种要求,处理肮脏琐碎的工作,还要面对管理层的刁难和质疑——他们可以随时搜查她的包裹,时刻寻找着她偷懒、偷窃、滥用药物的证据,他们有权要求他们不交头接耳,员工只能闭紧嘴巴工作,“这种投降式的举动已经超出了‘贫穷’问题,因为这会让人们毫无自由和尊严可言”。
底层工作者无由来地失去了其他阶级(甚至本阶级内部)的尊重,更失去了发出声音、表达自己的权利。在芭芭拉做女佣时,屋主似乎心怀敌意地鄙视她;当她结束工作,穿着制服去吃饭时,发现处于同样阶级的女侍甚至不会多看她们一眼。同事对芭芭拉说:“那是因为他们觉得我们笨。”在电视和大众媒体中,我们看不到任何关于这些拿着最低收入人群的身影。毕竟电视反映的,总是那个“每个人几乎都能赚15美元以上时薪的世界”,故事里“演的都是时装设计师、学校老师和律师”。从未被邀请进入那个幸福快乐的世界,底层人只能深深怀疑,是否是自己做错了什么。
“错”在哪里?生活困窘,是因他们懒惰、愚笨或者不够努力吗?
无论她如何兼职、跳槽及努力工作,处于社会底层的芭芭拉都无法维持最低程度的生活:在佛罗里达,她同时兼职两份餐厅工作,每天从早上八点工作到晚上十点,却只能栖身于2.4米宽的拖车屋里——这里被视为犯罪与吸毒者的温床;在缅因州,她平日做女佣,周末兼职老人院的饮食助手,她住在马桶和餐桌相距一米远的旅馆里,打电话求助慈善机构,大费周章获得免费食物,虽然只不过是些意大利面、烤豆子和蔬菜;在沃尔玛也同样如此,她继续工作,她去慈善机构求助,他们给了她许多糖果、饼干和火腿,建议她进入收容所。芭芭拉发现,当你落入困境,“穷人并没有什么神奇的理财方法”。她身边的同事的遭遇也并没有更好,只有忍受而已。
就像煤矿工人挖出的煤为人们供应能源一样,女佣打扫房间提供洁净的环境,女侍把食物送到客人的嘴边,店员整理货架方便顾客试穿——这些劳作构筑了世界正常运转的基础。然而,正如奥威尔在八十年前所言:他们维系了我们的生活,他们的存在却被遗忘了,他们被视为不存在。美国女作家芭芭拉在底层体验之后,呼吁所有人善待并尊重底层劳动者,因为他们“为了一份养不活自己的薪资而工作”,为他人做出了极大的牺牲:“她用自己的能力、健康和生命的一部分为代价,给你一份赠礼……他们忽视自己的孩子,好让其他人的孩子能有人照顾;他们生活在次等的住屋里,好让其他人的住家能闪亮而完美。”
他们受到伤害,为何沉默不语?
时间 | 2010s
地点 | 中国
记录者 | 袁凌
记录对象 | 中国底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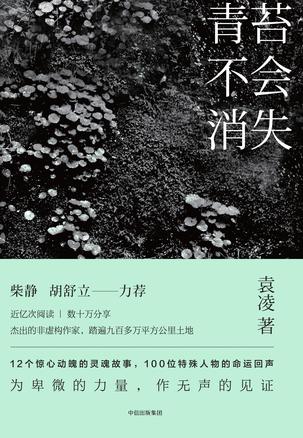
与奥威尔眼中英国无产阶级矿工生与死的悲剧性十分相似的,是中国记者袁凌在《青苔不会消失》中描述的中国底层世界。在他们之中,有因矿难受伤瘫痪的矿工,补助极低只能认命;有漂泊在北京艰难做生意的早餐小贩,在即将拆迁的早市和凋敝落后的家乡之间踟蹰;也有留守湘西农村的祖孙养猪人,世世代代无法跨越命运的门槛;还有被地雷炸残废了的农民,继续冒险在雷区中垦荒种田。
无一例外,他们从前卑微平常的生活,因为一场“注定的意外”而落入更加艰难的深渊。袁凌将目光置于他们劫后余生的日子上,他们的灾难和余生全都默默无闻,如同被“消音”了一般。然而他们又能如何?“大多时候,他们想要的权利,无非也就是能够继续沉默地生活。”
“生活剥夺了他们大部分的可能性,只留下了仅存的立足之地,又是看起来相当于一条蚕、一匹围绕磨盘的牲畜、一个除了内心发条不能移动的钟表的位置。”呈现这群人劫后余生卑微的生存方式,写作者袁凌似乎在收集他们经历伤害、侮辱、煎熬所表现出的顽强与坚忍,这令他想起自己的祖辈,想起他的“生活得如同他人背景”的外婆。他从苦痛中发掘着卑微的力量,就像股骨头坏死没有就医资格的女人,“微微佝偻中的重量”证明着一种“贴近生存地面的在世方式”。
然而现实是,这般沉默并非出于性格中的某种“逆来顺受”或是“坚韧不拔”,正如奥威尔书中的矿工们被指责“脏”或“臭”一样,他们,不得不如此。八仙镇的矿工王多权因矿难瘫痪,赔偿金两万,常年瘫卧在床;他一针一线刺绣,先是鞋垫,再是鞋子,后来是“家和万事兴”的巨幅十字绣;他多年没能办上残疾证,因为镇里民科的人说办这个证没有意义;汶川地震时他向县里捐献鞋垫并反映低保,民政局的人来了,送给他一辆轮椅,低保仍然没有回音,反而被改作工龄补助,由往年的村干部领取。“低保也要看能力”,镇上的能人说。
因在地下工作而得了尘肺的人,发不出什么声音,借钱洗肺,路费自付,因为他们从前在私人黑矿上工作,从没有什么合同和医保。即便是在国有矿劳动,工人被查出尘肺后也会被断然抛弃。少数走上维权之路的人将要面对“无数繁冗的程序和权势包庇的底层”,一直追究下去只会耽误就医,故也被看成一条“不归路”,还不如老老实实“预备好自己的死亡”。“中国大约有六百万尘肺病人,每年死亡人数是其他工伤死亡综述的三倍”,在令人心惊的死亡数字背后,是尘肺病人默默无声的苦捱。
最残酷的是,袁凌深切认识到,即使他们发出声音,或是用底层的一则悲惨故事偶然获得了轰动的新闻效应,并达到了不错的结果,比如“解决了某个具体的问题,甚至达成某种制度改良”,“底层的沉默”仍然无法改变,他们再次回到阴影中沉默生活,而一切诉苦之笔和抒情之词,对照现实都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三本书中三个时代的三种底层,面对着相似的贫穷、失声与无助。奥威尔说:“建立在矿产之上的社会,最终会忘记矿工的存在。”芭芭拉·艾伦瑞克说:“他们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获取微不足道的收入,而人们根本看不见他们。 ”袁凌说:“他们仍然只是生活剧场灰色的布景,是没有机会购票入场的主角”。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