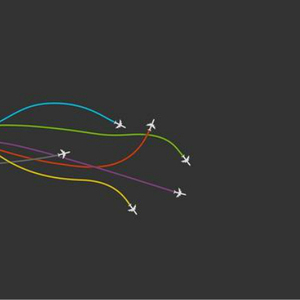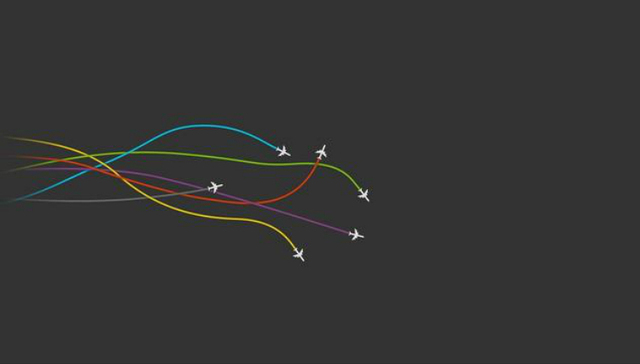新世相认为,「逃离北上广」是一个IP,这个说法,比较令人费解。
根据严格的理论定义,一种迄今仅仅策办了两场的活动主题——亦或是说某种城市情绪的疏导管道——能否产生完整的知识产权,这在全球都很难找到先例。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摇滚歌手约翰·列侬借着歌声唱出「要做爱,不要战争」(Make love not war),很快成为席卷西方世界的反战口号,围绕这个嬉皮士主张的衍生商品亦丰富起来——比如被广为制作和发售的徽章、以及大量借题发挥的艺术品——但是回首整个演变过程,也很难说有谁可以独占这套理念。
事实上,约翰·列侬还曾遭遇过一些社会活动家的「撕逼」,抨击他在歌词里剽窃了这句并不由其原创的文案,存在过度消费之嫌。
和第一届伍德斯托克音乐节足以吸引几十万「白左青年」在泥地里赤身裸体的交欢场面相比,缺乏动员能力的效仿只会沦为被风吹散的空喊,比如美国的保守主义政府就从来不曾放弃推广禁欲项目,不少虔诚的教会也强烈渲染婚前性行为的可怖,然而这种努力的收效看起来是滑稽而徒劳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所进行的联合调查发现,在曾承诺在婚前「禁欲」的12岁到18岁的成员中,有88%的人承认自己其实违背了诺言。
套用张伟为新世相锚定的概念——「我们终将改变潮水的方向」——熨贴人心的顺应时势,并准确的拿出符合情感需要的商品文化,这就是新世相在新媒体行业的独到竞争力,而「逃离北上广」则是最接近范本的一场连续实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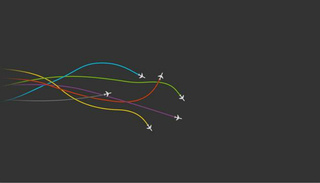
就像中国人难以理解半个多世纪前的美国人竟然上街反对国家的意志和决策——甚至还成功了——同时夹带性解放这个私货,美国人大概也不太明白中国在其经济日益强盛的关口,繁华都市里的年轻人却会为了甩开这一切而作出至少是象征性的表达。
唯一的共性在于焦虑,隔着迥异的时空,它渗入两代两地年轻人的每一寸毛孔,让人意识到与其相伴终究是无所适从的,无论是在地球反面发动一场劳民伤财且代价高昂的战争,还是为了追求生活品质而在自己身上安装蓄满压力的发条。
和约翰·列侬或是鲍勃·迪伦这代文艺工作者不同的是,新世相试图独自收割情绪催化的物质利益,如同在掌握潮水流动的方向之后,建立水力发电站对动能进行变现,无疑是门经济划算的买卖。
于是,「逃离北上广」要拍网剧了,拉来作为执行方入伙的,则是韩寒旗下的亭东文化。
一年前,《时尚先生》的总编李海鹏带着杂志的整个特稿部门投奔韩寒的亭东文化,在此之前,他所策动的两篇非虚构类特稿——《太平洋大逃杀》和《黑帮教父最后的敌人》——相继卖出百万级人民币的影视改编权,轰动一时。
内容产业的盛世,并不止步于自媒体的窸窣崛起,那些不愿直接将创作行为直接对接商业化的传统媒体人,同样设法找到为遒劲的笔力兑现价值的方法。
这里的一个悖论在于,在现有的新媒体运作体系里,内容成本的增长无法换来同等比例的回报增长,以去年秋季曾经刷爆社交网络的特稿《1986,生死漂流》为例,全网平台的流量补贴加起来,也打不平这篇稿件长达四个月时间的走访支出,更遑论难以计算的时间成本。
因此,整个商业模式的摸索,就变成了波纹式的递进:依靠内容本身的重量,在社交湖泊的水面全力砸出水花,逐层构建公众层面的认知力和影响力,最终再由成熟的产业链加入,整体性的收集全部能量,进行二段售卖。
再最后的环节,所谓的成熟产业链,原本是出版业,早期的天涯社区、晋江文学和豆瓣社区,都不乏编辑长期「蹲守」,致力于说服热帖作者将作品印刷成书。只是,在产业发展、回报效率和市场空间多个角度,影视业近年以来都更加匹配这个位置,它也承接下了搜刮故事的主要工作。
李海鹏就自诩为「故事买手」,他手握两套生产资源的班底——韩寒办了五年的数字发行应用《ONE》和与其保持密切联系的传统媒体同行——却依然在供应端多有捉襟见肘之处。
不是缺少好的内容,而是并非所有好的内容都有IP价值,用李海鹏的话来说,它的本质是「将一种影响力转化为另一种影响力」,前面的影响力不够明显,后面的影响力就无从谈起。
所以,尽管就总量而言,数字都是极为鼓舞人心的——《ONE》的故事库存超过1500篇,豆瓣更是宣称自己攒了800部原创内容亟待「改嫁」——只是分母的规模委实没有那么重要,能够将投资风险降到最低的分子数量才是关键。
而「逃离北上广」的优势恰好呈现出来:这是一个自带流量的故事容器。
在张伟的最初设想里,「逃离北上广」的意义远远不如现在这般宏大,甚至带有一些暧昧的争议:它究竟只是为「航班管家」量身定做的一场营销事件——这意味着新世相的角色只是承办之一的乙方——还是由新世相主导的社群运营选题,只是顺带着接受了一家企业提供的赞助?
事实可能偏向后者,似乎是为了验证「逃离北上广」的可复制能力,在决定启动同题网剧项目之前,张伟做了「逃离北上广」的第二季,依然是数量有限的机票,依然是清晨推送的通告,不同的是这次的合作企业达到了八家,鲜衣怒马,毫不掩饰。
批评言称的审美疲劳和套路雷同,在张伟看来正是「逃离北上广」的最大价值,它就是可以证明,作为一个能够产生真实动员效果的标语,它就是可被重复使用的,「可以好几次的踏入同一条河流。」
这也符合辨别IP特征的一道标准:是一次性的从绽放到枯萎,还是有着一岁一枯荣的生命力。
不过,「逃离北上广」还无法构成内容本身,它更像是一个制造内容的机遇,如同公路片的类型,旅程的起点和终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参与的人,以及中途遇到的风景和故事。
因此,比特稿改编影视更加多元的操作模式出现了,新世相以组织者而非创作者的身份将「逃离北上广」当作一款文化产品,并遴选出亭东文化这个具有一致目标的联合运营商,最后输出给对内容高度饥渴的在线视频平台。
BBC的特约撰稿人肯·塔克曾在解释为何「权力的游戏」能够风靡全球时这样说道:
「在这样一个人们每日生怕惹恼老板而被迫回到令人恐惧的求职市场,或精打细算偿还按揭的时代,看着逃避主义电视剧中那可被畅快干掉的领导,整部剧马上散发迷人魅力。人们对复仇和胜利的幻想无比现实——每个人都有共鸣,即使你知道永远无法命令火龙为你效命。」
尽管内容味道大相径庭,但是「逃离北上广」的魅力,也同样在于这种代理叙事的精密设计,它直接感染着和新世相保持活跃联系的两百万用户,以及围绕他们的几何级数的社交蛛网。
能否真的逃脱以北京、上海和广州为代表的一线城市经济体并不值得使用死理性派的态度较劲——各方争论不过都是助燃火焰的薪柴——在张伟看来,用户愿和新世相共同行动的认同基础,是「逃离北上广」何以成为IP的根本原因。
虽然张伟不无「客套」的说新世相的做法可以在很多内容创业公司得到流水线式的复制,但他又讨厌新世相成为一家「容易被定义」的公司,不想错过更多的可能性。
比如新世相提出的品牌加上社群两大内容引擎,就与通俗意义上的同类概念差别很大,这里的品牌,指的是内容的前置货币化能力,无论是「逃离北上广」还是其他的策办事件,新世相都能够预先找到愿意帮它收回成本的赞助方,这极大的降低了经营风险,而社群则是以近乎零成本的为新世相贡献参与能力的用户集合,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的一切内容和温度,则又给了新世相挑拣选拔和二度变现的机会。
这个结构的最大亮点,在于新世相始终位于相对安全的位置,进退得当,游刃有余,无论涉足有多广袤,都能够量力而行。
有的时候,会把新世相和活跃在中世纪的吟游诗人的形象叠合起来,那些带着风笛和弦琴的年轻人游荡在平原、森林和村庄之间,他们收集一个又一个传说,并向四野八荒弹唱传述,贵族向其给予礼遇和施恩,平民为其分享食宿和尊敬,只要还能行走,他们的征程就永远不会停下。
虽说歌伶的把戏从来都不足以取悦上帝,但它所佐证的,也永远都只是落英缤纷的人间百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