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和精神源泉。逃离大城市、回归自然与田园,河水变黑变臭,雾霾困扰,癌症小镇,滥伐树木,土地荒漠化,杀戮野牛鲸鱼,物种加速灭绝,噪音污染,温室效应,冰川退缩……二百年来,这些问题都曾在美国发生过,或依旧存在着。
《荒野行吟》这本书以美国二百年来形成的自然文学流派发展脉络为线索,叙说了一场余韵悠长的“返乡”之旅。作者撷取美国自然文学发展中的重要代表人物和主要作品,立足美国,又不唯美国,将视野放入地球自然发展史;立足作品,又不唯作品,将自己所思所想涵盖其中。通过行思结合,图文并茂,发见自然生存的窘态,勾勒自然历史发展图景,为活色生香的荒野或自然找寻一个存在的理由。
睡谷,一则梦想预言
确实是天堂生活!我敢肯定说:世界上没有别的人——至少在我们新英格兰这个荒凉的小天地里没有别的人——在那些日子里曾经梦想过天堂生活;要么只有像南北极的人对热带地方所做的那种梦想。
——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睡谷,即福谷,只是中文译法不同而已。在此,纳撒尼尔·霍桑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发生在福谷里的“乌托邦”故事。我本以为,福谷只是霍桑的社会改革小说《福谷传奇》故事中虚构的一个地方。后来读华盛顿·欧文,在他的散文《福谷的传说》中,睡谷成了一个真真切切的地名。
19世纪初,为了人的完善,美国一些相信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势力建立了众多“乌托邦社区” 。睡谷,曾经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华盛顿·欧文说,睡谷是一个小村庄,世上最宁静的地带之一。它坐落于纽约以北、波士顿以西、哈德逊河东岸的一个山坳之中。在欧文笔下,睡谷之地,波凯蒂科河穿过林地,河岸草地清新翠绿,岸上遍布着山毛榉、栗子树和一些小灌木,呈现出一种亘古不变的静谧,是一处典型的新英格兰式秘境。实际上,这个地方是当年新大陆荷兰移民居住的隐僻小山谷。然而,正是在这样一个不太起眼的小山村,因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引发了一场涉及美国社会进程的大思考、大变革。

睡谷之意,顾名思义,能令人昏昏欲睡、意象朦胧之土地。于是,睡谷在人们心目中便笼罩着一股魔力,继而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乐贝国” ,即理想王国。其时代背景则是美国的工业化进程,人与自然的关系被迅速解构。
1832年,美国修筑了历史上第一条铁路。当时的作家丹尼尔·韦伯斯特这样写道:我们看到蒸汽动力横渡大海,穿越大地,电流传递着信息。这是个奇迹般的时代。……时代的进步几乎超越了人类的信念。

时代的进步几乎超越了人类的信念
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于美国新英格兰地区。面对这种变革,以及在这种变革的影响下,许多人选择了回归自然。许多作家亦拿起笔,以“从社会退隐到理想化的自然风景”为核心主题进行创作,于是便有了“睡谷传奇”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有爱默生和梭罗。涌现出来的作家有库柏、麦尔维尔、福克纳以及弗罗斯特等等。纳撒尼尔·霍桑是其中之一,他创作了长篇小说《红字》 《带七个尖角阁的房子》和《福谷传奇》 。尽管让霍桑更出名的是因为他记录了当年铁路侵袭“睡谷”的事件,但并不妨碍他在新英格兰鼎盛时期的所有作家之中,最有可能变得“永垂不朽” 。而这种“不朽”当然也包括他的代表作《福谷传奇》。
从托马斯·杰斐逊时代开始,美国理想,或者说美国人的基本意象便是乡村田园景致。在当时美国人的心目中,这种“乡村风景”便是“纯洁而简单的净土” ,一种典型的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式的模式——退出大千世界,在清新而葱翠的风景中开始新生活。主旨当然是大自然——或一个个小村庄,或一间间林中独立的农舍——前面有牧场,有蜿蜒的小溪,附近有吃草的牛羊;高地上有密集的榆树或森林;远处,在西边的地平线上,群山朦胧,连绵起伏……
或许是受到 17 世纪早期康帕内拉《太阳城》和安德烈《基督徒城》等乌托邦思想的影响,纳撒尼尔·霍桑在《福谷传奇》一书中寻找或虚构的便是这样一个“世外桃源” 。乌托邦,唤起了情感。曾经,纳撒尼尔·霍桑借住了爱默生位于康科德的古屋四年。在那里,他从孤独与反省中获得解放,终于在近四十岁的时候成为“一个真正存在的、在这个世界上有家可归的人” 。古屋是一个环境优雅的地方,周边种满了梨树、桃树和苹果树。在房子的林荫道旁,绿杨低垂,绿树成荫。于是,霍桑在此种植白菜、南瓜、黄瓜、豌豆、玉蜀黍等,构思自己的小说,激发创作灵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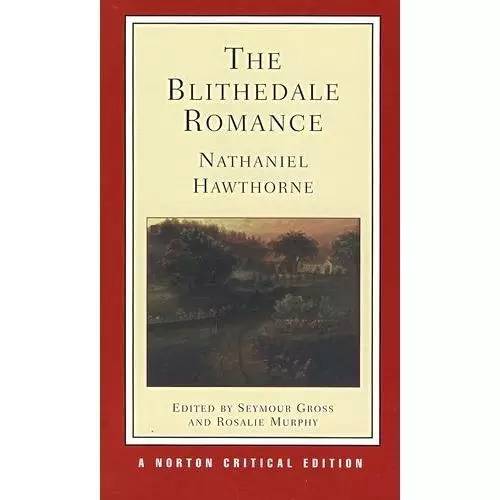
但是,霍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位小说家, 《福谷传奇》也不是一本小说。的确,就《福谷传奇》的题材来说,虽说还是小说的形式,但其中的人物,并非都是虚构,故事中迈尔士·卡佛台尔的原型便是霍桑自己,齐诺比娅的原型据说还是19世纪美国作家、 《日晷》杂志主编玛格丽特·富勒。故事讲述的是,为了追求天堂般的生活,一群来自城里的向往淳朴田园生活的理想家,诸如怀抱着伟大梦想、拥有俗世高贵性格的慈善家霍林华斯,洋溢着强烈热情并绝顶美貌的齐诺比娅,以及奇异虚弱且漂亮妩媚的蒲丽丝拉等,当然也包括卡佛台尔,他们离开了城市,带着内心的苦闷,来到福谷,进行一场伟大的思想实验。
这是一群傅立叶“法郎吉”式空想主义者,但又不全是。他们深受爱默生散文、《日晷》杂志、卡莱尔著作和乔治·桑小说的影响,尤其崇尚傅立叶“建立科学的有组织的协作社区消除贫困”的主张。他们分析傅立叶主义与自己所奉行主义之间的不同,目的是寻找幽静的生活。他们来到福谷的初衷,是想在此创建一种新的生活范式,创立“福谷社” ,建设一个“共产团体” ,以此摆脱现实社会的束缚,并重返朴素的自然。于是,从一开始他们的生活便充满了浪漫色彩,像农民那样装束自己,身穿麻布罩衫、格子花衬衫和条纹裤子,头戴薄木片编成的帽子,手持粗糙的胡桃木手杖。在这种理想的环境里,人们不会受到“虚伪和残酷的主义统治” ,能够抛弃自傲的情绪,亲密友爱。通过减轻劳力负担,用自己的力所能及,相互依靠着去做该做的工作,而不是用暴力、诡计或巧取豪夺获取利益。
人们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我们的光亮的窗口。在风雪交加的夜里,在一片黑暗中看到一团强烈的火光,对一个单身旅客说来,是再愉快、再兴奋不过的事情了。任何人看到这些闪烁着红光的窗子,都会感到高兴的。我们为人类燃点的烽火不是使他们显得很温暖很幸福吗?(杨万、侯巩译,下同)
福谷,就是这样一个罗曼蒂克之地。在霍桑笔下,农场周边还有一些赏心悦目的起伏山峦,一条小路向草原或森林延伸。清寒明澈的河流,环绕着草原。土角之间,夹着一湾流水,河水荡漾着两岸的芦苇。枝叶蔽空的白桦林,阳光闪耀。这里的土地,可以种植马铃薯、玉米和根菜作物,能够让劳动者自给自足。白色的村落,红苹果、紫葡萄果园,一片片森林,充满了自然野趣。林中有松鸡和松鼠出没,小河里有鱼儿和野鸭嬉戏。

一个罗曼蒂克之地
这是一个幸福的生活场景。慈善家霍林华斯是小说中一个重要角色,也是这种田园理想的设计者和推动者。按照他的宏伟计划,他要在福谷实现一个改造人的计划——利用道德、理智和勤劳的力量,以及纯洁、谦虚和高尚的心灵,建立一种更有价值的生活范式。或者说,依靠农业劳动,让人们过上一种“简朴的、农村风味”的新生活。这种理想,使那里的人们都有公民意识,能与自然和谐相处,最终实现“理想的平等社会” 。的确,经过一段时间的体验,他们的这种田野生活似乎还发展得不错——一个个面孔晒得黑黝黝的,胸围扩大了,肩膀变得又宽又结实。对于基本劳动工具——犁、锹、镰刀、干草耙等,他们运用自如。
锹子每次铲土都在发掘一些至今还见不到阳光的“智慧”的芬芳的根源;在田地里歇一歇,让风吹干自己额角上的湿汗,抬头张望,似乎可以看见遥远的真理的灵魂……
此时的福谷,青春的活力像灿烂的阳光一样照耀在长满枯草的荒滩上……
理想家们所从事的伟大实验能否成功?结论当然是否定的。作品一波三折,人与自然和谐的理想终于在现实面前败下阵来。最终,故事中的各式角色失望别离。霍林华斯们“用尽力气、翻了又翻的泥块始终没有感化成为思想” 。
自负、激情并执着的齐诺比娅是小说中的悲剧人物。在经历了这样一段所谓诗意般田园生活之后,回到现实之中,她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呐喊:
什么慈善和进步……我们在努力建设一种真正的生活制度的时候,无疑地我们都造成了各种可笑的生活中间最空虚的笑柄。……这的确是一场无聊的梦!然而,在那儿的时候,它也确实给了我们一个愉快的夏天,和一些光明的希望。它不能够再起什么作用了,我们不必为了一个破碎的泡影而流泪吧。
随着时光流逝,生活在福谷的人们日子过得逐渐暗淡,或者说生活成为“一个破碎的泡影” 。我——霍桑——卡佛台尔,审视着这个因梦想而建立的崇高无私、美好的生活制度。他反思这种尝试,这种失败的尝试,从一开始的傅立叶主义,到后来对高贵精神的背叛,直至走向死亡。齐诺比娅之死,使卡佛台尔最终认识到了人类情感的复杂性,以及这种社会实验失败的必然性。

翻了又翻的泥块始终没有感化成为思想
作者纳撒尼尔·霍桑将此比喻成一场梦——当梦境演变为悲剧的时候,哀伤的氛围便迅速打破了脆弱的噩梦,一切都消失了。最后,霍桑甚至都不肯承认曾经有过福谷这个地方,或者说福谷根本就不曾有过。那里没有任何自己回忆中的那种颇具意义的劳动团体,它是一场梦、一幕幻景。那里成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在此意义上,霍桑坦承,从摸索人们心中暗藏着的情感出发,这个尝试可能还不能算作是完全的失败。此时的霍桑充满了矛盾、迷茫和困惑。后来,作家比尔·麦克基本在谈及这种现象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传统的乌托邦观念根本就于事无补。人们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理想,是由于承受了太多,或者拥挤,或者压力,或者缺乏有意义的工作,正是这种或者太多或者太少,造成了这种社会恶果。至此,要求推翻现有社会秩序、代之以平等主义的乌托邦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和无法调和的矛盾。
霍桑毕竟是一位心理描写大师,他用细腻准确的语言,深刻揭示了其中人物的内心冲突与心理变化,以及对“乌托邦”改良尝试的失望。事实上,短期看,这种乌托邦理想的确能刺激理想者前进,但长期看,在接触农场并熟悉农场的运转体制之后,最终带来的必然是绝望。小说情节曲折离奇,意象构思精巧,阅读过程让人欲罢不能。正如波兰学者布罗尼斯拉夫·巴茨克所说,在这个矛盾心态交杂的时代,人们“一方面对乌托邦理想充满了不信任,一方面又渴望一座乌托邦” 。《福谷传奇》的结尾,作者并没有为读者设计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事实上他也无法得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作者构思这个寓言般的故事,深刻刻画了在通过人的力量来主宰世界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巨大矛盾,生动地再现了自然、社会与人性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约束。它使我们认识到,一种理想的风景所象征的那些追求,不会、也不可能体现在传统的体制之中;它意味着那个所谓人道的社会愿景,已经演变成了一种个人苟活的标志。自然蓝图再美好,都无法改变人自私、欲望和软弱的缺陷。最后,书中的主人公要么死去,要么在社会中异化,变得孤寂无力。
现实中,当人们邀请拉尔夫·爱默生加入类似这样一个农庄团体时,被爱默生断然拒绝。他说,我不能“从我现在的牢房中走向一座更大的监狱” 。尽管他确信科学与技术在美国的环境下可以用来为乡村理想服务,但他只相信“纯粹的事实”。倒是亨利·梭罗进行了一次这样的试验。他曾经关注过位于睡谷的布鲁克农场和弗鲁特兰兹果树园。梭罗的关注点在于个人应当如何生活,如何与邻居交往。在此意义上,重情感的梭罗有别于重法则的爱默生。的确,在人类未来如何重构的问题上,梭罗的观念似乎更趋理性与人性。在《乌托邦的想象》一文中,梭罗在强调构建未来外在世界的同时,更加主张让人回归自身,回归人类的本性,注重内在心灵的升华。在此意义上,困惑的霍桑与梭罗似乎找到了更多的共识。霍桑去世后,他选择与梭罗葬于同一“睡谷”公墓,成为最终的“生死兄弟” 。

人们充满了不信任,又渴望一座乌托邦
一百余年前,像一个孤独地站在岗位上的哨兵的霍桑,他所发出的呼喊,就好像是从旧日碎瓦颓垣中发出的悲鸣。美好的自然与扭曲的人性之间形成了巨大反差。一面是乡村世界的安宁与纯朴,另一面是城市世界的喧嚣与世故。霍桑对工业化与人性的现代性思考和关注,意味深长。乌托邦的故事至此并没有结束,20 世纪 70年代末,随着美国“嬉皮运动”基本终结,一部分不愿意重返“社会体制”的人,前往偏远的阿拉斯加,他们开疆辟土,建立了一小片属于自己的“伊甸园” ,到 90 年代末,这些人把乐园发展成为“生态观光业” 。后来,关于乌托邦的理论与实践,甚至出现了诸如赫胥黎“岛国”式正乌托邦和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式反乌托邦流派之别。再后,欧内斯特·卡伦巴赫出版《生态乌托邦》一书,作为现代意义上乌托邦的一种类型,卡伦巴赫以人们“在继续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各种好处的同时,人类社会与其环境和谐相处的可能性”为主题进行探索。他甚至设计将美国的北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和华盛顿等州脱离联邦政府,构建一个与世隔绝的生态乌托邦社会。而塞缪尔·莫恩在《最后的乌托邦》一书中,描述了乌托邦理想的新趋势。如在美国,20 世纪以后,不少本土社团被呼唤了起来,拯救正深陷于消费主义的美利坚。
人类向何处去?一百多年之后,这一命题在人们的思考中继续“发酵” 。霍桑所讲述的故事并没有结束,我觉得,它仅仅是一个开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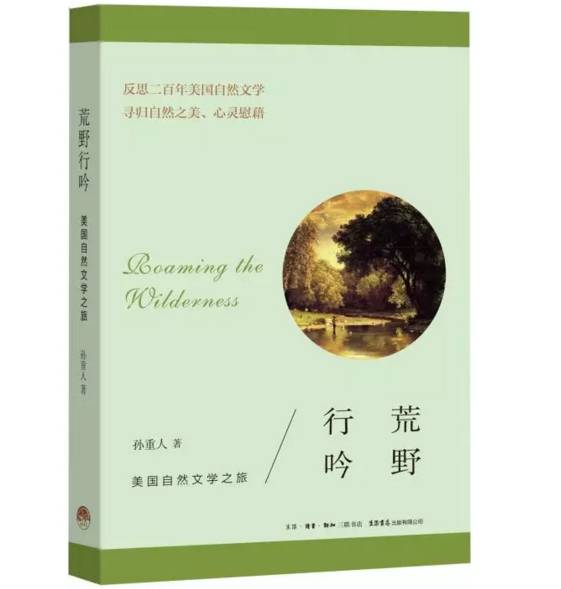
《荒野行吟》 孙重人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生活书店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