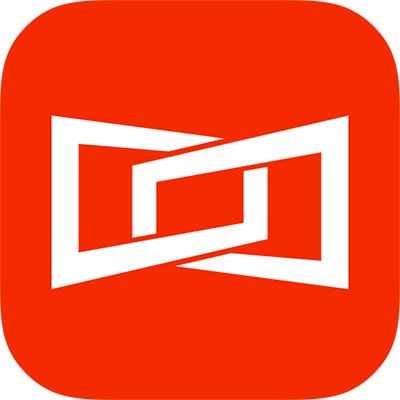文|南都观察
好友向我抱怨,这次疫情让她与好几个朋友“决裂”。我苦笑答道,我也是。
作为一个不爱朋友圈的人,这次疫情我更新频率快了许多,尤其是在发生一些热点事件后,会转发大量消息到朋友圈。但也接收到不少留言,站在跟我完全不同的立场,他们纷纷劝我,“不要在朋友圈一直转发负能量”、“没想到你也是愤青,我觉得你太偏激了”、“你为什么就不能理解一些政策的苦心呢?为了大局,总有人要牺牲的呀”……
鉴于朋友圈里本来有些人就不算是朋友,何况他们本身是各种“震惊体”的爱好者,看到他国疫情超过,就惊喜地“反超了!”看到美国感染人数破10万,就幸灾乐祸地“破10万!”我只能先删为敬了。
一个让生活暂时陷入停摆的疫情,也是一面照妖镜,让我们看到了众生相。一张武汉人领骨灰盒的照片,都能让一部分人感到不快,“这个时候你发这样的照片,别有用心啊”。我和朋友不约而同地感到:原来太多太多人,缺乏对他人痛苦最基本的共情能力。
我所理解的共情,就是你所经历的不幸、你所感受到的痛苦,虽然看似与我无关,但我能感同身受,并站在你的立场上,理解你的吁求,并试着力所能及地帮助你。
共情之所以不只是同情,是因为后者可能只是一种高高在上的视角,或者隔岸观火。他知道你很“可怜”,也动过恻隐之心,甚至也掉下眼泪,但就局限于此。
共情超越同情的地方在于,同情可能发生在“我”和“你”之间,但你是你我是我;共情是让“我”和“你”成为“我们”,这个“我们”大于不同理念、信仰与价值体系的分歧,它指向的是更普适的东西,比如生而为人的权利、尊严和自由。
如果换用政治学者周濂的一个说法,同情是一个伦理学的概念,“所有的屈辱、苦难和不幸要么来自一地鸡毛的伦常纠葛,要么来自晴天霹雳的无常命运,前者的道理说不清楚,后者的道理没处可说,于是乎中国式好人对于‘为什么’的追问最后只能化约为认命。”我很同情你的遭遇,但如果不幸降临了,也只能受着了。
共情更像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它指向的是“何以至此”的追问。周濂指出,“通常认为政治哲学只探讨两个问题,一个是‘谁得到了什么’,一个是‘谁说了算’,前者指的是权利和利益的分配问题,也就是‘正义’问题,后者指的是权力的‘合法性’问题。”
换句话说,个体所经历的不幸,是否涉嫌权利被侵犯的不正义,某些碾压个体权利的决策,是否充分合法?共情不只是朴素人道主义立场同情苦难,也试着追究不幸的形成机制。它不仅有鸡蛋的视角,更有鸡蛋的立场。
但只要翻阅微博评论就会发现,太多人失去了共情能力。他们也愤怒于老人被打,但他们更担心有人“带节奏”;他们也能理解失去亲人者的哀嚎,但更担心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他们也不见得完全不同意方方的看法,但更担心“境外势力”炒作……
很难说他们是坏人,他们也同情不幸者的遭遇,但有另外一个无形的“集体”的概念统治着他们的思维,让他们认为有东西比个体的具体的苦难更重要。
如果说,共情里的“我们”,是关注每一个个体具体的苦难,那么丧失共情者所拥护的“集体”,里头有的只是一个个面目模糊的个体,个体的悲欢喜乐并没那么重要,“集体”的目标和方向才是重要的。
换用哈耶克的说法,“我们”与“集体”的差别在于,集体“想组织整个社会及其资源达到这个单一目标,而拒绝承认个人目的至高无上的自主领域,”“社会为之组织起来的‘社会目标’或‘共同目的’,通常被含糊其词地表达成‘公共利益’、‘全体福利’或‘全体利益’。无须多少思考便可看出,这些词语没有充分明确的意义以决定具体的行动方针。
千百万人的福利和幸福不能单凭一个多寡的尺度来衡量……根据一个单一的计划指导我们的一切活动,就预先假定了我们的每一种需要都在一个价值序列中占有一个等级,这个价值序列必须十分完整,足以使计划者在必须加以选择的各种不同的方针中有可能做出决定。”也即,“集体”面前无个人。
这个“集体”具体是什么?埃里克·霍弗在《狂热分子》里写道,“被完全同化到集体里去的个人不会把自己或别人视为人类。当被问到他是谁的时候,他会自然而然回答说他是德国人、俄国人、日本人或基督徒、佛教徒、某一部族或家族的一员。”
他们所心心念念的“集体”,指向的是宏大机构、宏大目标、宏大身份与宏大叙事。应该强调的是,人们诉诸于“集体”,并不总是错的;人们渴望在“宏大叙事”里找到某种情感归宿,也完全可以理解;甚至有人愿意为了理念而牺牲自我,也可能是高尚而纯粹的。
我们反对的从来不是“宏大”或“集体”本身,我们反对的是某一类人,他们看到的、拥护的、热爱的,是一个宏大的但可能是空洞的理念,这让他们看不到一个个具体的人。或者说,他们认为只要为了“集体”,就可以任意“牺牲”他人的权益。
有些人虽然无法共情,但起码有同情;而有些人不仅无法共情,当彻底被“集体”蒙蔽,他们连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同情也没有了。“集体”至上,任何可能影响集体光辉的言行举止,都被冠上“阴谋论”,随之而来的就是非我族类、党同伐异。
那些“集体”至上者总是认为,“集体”好了,个体一定会好的,这的确是某部分事实。可问题是,当“集体”既不正义也不合法地牺牲了个体的权益时,他又该如何保证,自己不是下一个牺牲者?
作家韩少功说,这种心理顽疾叫“自我机会高估”。他们总是认为,个体的不幸那是概率极小的事情,压根就不会落到自己头上。“所有输家的‘候补赢家’心态,最终支持了赢家的通吃;所有输家那里‘别人遭殃’的预期,使自己最终被别人快意地剥夺。在这个意义上,自我机会高估意味着人们自寻绝路,意味着我们的敌人其实源于我们自己,”韩少功说,“自我机会高估不仅支撑赌业,也是诸多强权和罪恶的基础。”
要看到一个个具体的个体,要允许他们有悲伤的权利、有申诉的权利、有追问的权利、有质疑的权利、有呼救的权利、有说出不同意见的权利。
我希望“你”和“我”能看到彼此、感受到彼此,希望“你”和“我”会成为“我们”。每一个“你”所经历、所感受的,也是“我”可能会经历和感受的,就像家人有苦痛,我们也会辗转反侧、会伤心难过。
个体常常独木难支,但“我们”是有力量的,“我们”发声了、行动了,才能尽可能避免“集体”一刀切地湮没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