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数人眼中,诗人布罗茨基的一生由黑白分明的两段构成。32岁之前,他是苏联小有名气的地下诗人,由于在非主流文学杂志上发表诗作以及与外国作家来往,布罗茨基受到当局的监视,并在随后以“社会寄生虫”的罪名被起诉,流放至苏联北疆服役。这一事件正值东西方冷战时期,布罗茨基也因此成为了世界的焦点。32岁那年,布罗茨基被苏联当局驱逐出境,从此开始了客居美国的后半生。在诗歌《一九八零年五月二十四日》中,他写下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
由于缺乏野兽,我闯入铁笼里充数,
把刑期和番号刻在铺位和椽木上,
生活在海边,在绿洲中玩纸牌,
跟那些穿燕尾服、鬼才知道是谁的人一起吃块菌。
从冰川的高处我观看半个世界,地球的
阔度。两次溺水,三次让利刀刮我的本性。
离开生我养我的国家。
幸运的是,正是这场轰动一时的流亡使布罗茨基彻底从地下解放,进入公众的视野。在美国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他不仅先后出版了多部诗集和散文集,还因“广阔的思想和浓郁的诗意”获得了198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如今,布罗茨基已被公认为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俄语诗人之一,俄国学界甚至将其与普希金并列。但直至去世,布罗茨基也未返回祖国。在散文集《水印》中,他如此总结自己的“前世”与“今生”:“为了拥有另一种人生,我们应该结束第一种人生,而且这个活儿应该处理得干净利落。没有哪个人能够令人信服地实现这种事,尽管有时,不辞而别的另一半或是政治体制确实会帮我们大忙。”
布罗茨基虽与曼杰施坦姆、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同属俄国古典主义诗人,但其作品的表现手法却明显多了些西方文化的痕迹。在许多公开演讲和诗歌评论中,布罗茨基都提到过弗洛斯特和奥登等英语诗人对他的影响。有趣的是,在西方文学界乃至整个世界,布罗茨基最广受推崇的作品却不是他的诗歌,而是他的散文。他在生前出版的三部散文集《小于一》(1986)、《水印》(1992)和《悲伤与理智》(1995)均以英文首版,这也是中国读者最为熟知的几部作品。反观布罗茨基的诗歌,绝大多数仍以俄语创作、发表,这似乎暗含了诗人对于诗歌语言之本质,以及诗人与语言之关系的独特理解。
在日前出版的《布罗茨基谈话录》一书中,同为俄裔美国作家的所罗门·沃尔科夫尝试以对谈的形式为读者勾勒出布罗茨基一生的走向、他的创作路径,以及他对20世纪诗歌的理解与洞察。回顾定居纽约的生活时,布罗茨基谈到了他是如何重塑自己的语言体系和创作观念的。对于他来说,诗歌是语言存在的最高形式,而俄语和英语则是观察世界的两种方法,如同“坐在一座山的峰顶上,看着两侧的山坡”。如何跳出历史与命运,在东西方文化之中确认书写的价值,是身为“流亡诗人”的重要议题。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书中节选相关内容,以飨读者。
《在纽约的生活》

文 | 约瑟夫·布罗茨基 所罗门·沃尔科夫 译 | 刘文飞
沃尔科夫:您已经在纽约住了很多年,在这个带有波希米亚风格的优雅街区里扎下了根。在这里,大家全都认识您,您也认识所有的人。您的生活,至少从表面上看,是非常舒适的,起居也很有规律。您是不是觉得,比起在苏联的时候,这里的生活要更有预见性一些,更为稳定一些?
布罗茨基:是,又不是。更确切地说,不是。
沃尔科夫:为什么?
布罗茨基:天知道为什么。首先是因为,你在这里过的并不是什么外在的生活。预见性有什么不好呢?它就体现在你和外在世界的关系之中,这个外在世界也就是你的住处、职业和周围的人。可是第一,对于这种预见性来说,纽约可是太多样了。在这里,永远存在着某种面容上的万花筒。这样一来,预见性的效果就要大打折扣,虽说是局部意义上的。第二,我在内心上并不依赖于我在街道、地铁、大学等地所遭遇的一切。虽说这些周围环境有时也会让我心生厌恶。我不想说,我在过着某种多样的、丰富的内在生活,但是就整体而言,在我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主要都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在这里,在西方。这种内在生活的程度还超过了在苏联的时候。或许是因为,这里的环境毕竟有些陌生,是这样的吗?从我这一方面来说,这要么是一种保护反应,要么是……
沃尔科夫:自我封闭……
布罗茨基:当你把注意力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上的时候,即对于你来说什么是最为重要的,这里已经有了某种单调,不是要把它完全去除,可是……此外,在我这门手艺中,在文学中,所做的工作或多或少都要被投射到生活中去。生活于是便对你在纸张上所做的一切开始产生依赖了。如果说,某些情景的重复在生活中还是可能的话,那么在纸张上,这样的重复却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在文学或艺术中,这种重复就会被称为“陈词滥调”,是这样的吗?你在文学中会避免这样的陈词滥调,同样,在正常的日常生活中,你也会竭力回避这类重复。也就是说,似乎在进行一种永不回头的线性运动。
沃尔科夫:您好像对我说过,您不愿意把自己的生活划分为好几个时期。如果这里指的是内在的生活呢?
布罗茨基:这是一个很出色的问题,所罗门,可是回答起来却很困难,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我从未认真地审视过自己。这无论如何都不是卖弄。一般来说,内在的变化是不可能被跟踪的,如果这些变化还谈不上质变的话。有些变化在发生的时候,你自己往往是觉察不到的。
沃尔科夫:在生活中还是在纸张上?
布罗茨基:在大脑里。但是,恰恰是在写作的时候,当你突然写到什么地方的时候,会觉察出这一点。这个时候,你的脑袋里会冒出一句什么话来,对于你的内心状态而言,这句话往往是真实的,是这样的吗?我非常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个瞬间,那是在1962年。我写了一首诗:《新房客对家中的一切都感到陌生》。事实上,这里所谈的当然不是房客,而是一种比喻。因为我突然明白,并不是我成了一个全新的人,而是另一个灵魂移居进了我的身体。我突然意识到,我成了另一个我。从那个时候起,我似乎就不再有什么变化了。

沃尔科夫:一位诗人居住在异国他乡,却继续用母语写作,他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布罗茨基: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似乎,托马斯·曼在迁居到这里、迁居到美国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我在哪里,哪里就有优美的德文。”就是这样。
沃尔科夫:可是要知道,散文和诗歌之间毕竟存在着某种差异。
布罗茨基:诗歌方面的事情当然要更复杂一些。因为散文就是讲故事……在散文中,有那种似乎能帮上大忙的机械因素。我不太清楚,我从未专心写过小说。说到写诗,这当然要稍难一些。为了能写出诗来,就需要在语言的习惯中持续不断地熬煮。也就是说,要持续不断地谛听这些习语——在美食店里,在有轨电车里,在啤酒馆里,在排队的时候,如此等等。或者是,对这些习语充耳不闻。问题在于,住在纽约,你就处在一种模棱两可的状态中。一方面,电话打来打去,一切仿佛都在继续。另一方面,又没有任何东西还在继续。就是这样一种虚假的状态。或许会更好一些,如果完全听不到母语的话。或者相反,如果能更经常地听到母语。更经常地听到,这又不可能。是吗?如果没有给自己制造出一个人为的环境。当然,你可以遇到一些来自俄国的人,可以与他们交谈。不过,这照例是一种被迫的选择,一种被迫的语言运用。更不用说,我有时不得不和这样一些人打交道,即便是在家里,我也许都不想和他们说话。事实上,重要的并不是一个人用什么样的语言说话,而在于他说的是什么。就这一意义而言,这里的处境一点也不比在祖国的时候更好。
沃尔科夫:我正想问一问这个问题。您感觉到了吗,纽约就是纽约,而不是新英格兰,它正小心翼翼地、逐渐地在您的诗歌中占据地盘?或者,它依然是这种意义上的异乡?
布罗茨基:如果认真地说,彼得堡的风景如此的古典主义,似乎成了一个人内心状态和心理反应的等价物,或者至少可以说,这个人的反应是作者反应的等价物,这是一种完全可以被意识到的节奏,甚或是一种自然的生物学节奏。在这里所创造的一切,似乎处于另一个维度。在心理上把握这一点,也就是说,把这一点转化为自己的内心节奏,我认为简直是不可能的。至少,对于我来说是不可能的。我对此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应该说,还没有任何人做到这一点,不仅是一个比如说来这里做客的人,就是一个当地人也做不到。只有哈特·克莱恩在他的《桥》中作过某种尝试,想把纽约熬煮一番,塞到美文中去。这是一首很出色的诗。那里什么都有……但是,纽约还是没有被以一种自然而然的方式写进诗歌。这不可能做到,似乎也没有必要做到。如果漫画中的超人写起诗来,他或许能成功地描写一番纽约。
沃尔科夫:难道其他的诗人都没有写过这个主题?
布罗茨基:我只记得一个非常认真的尝试,做出这一尝试的是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不过在我看来,这个尝试也没有获得什么成果。除了一个出色的比喻——“灰色的嘴唇”,或者其他一些诸如此类的东西。因为,当你拉开一段距离,用某种陌生化的眼光来看纽约的全景,它的确像一片嘴唇。

沃尔科夫:我还记得,在和您的一次谈话中,您的一句话像针一样刺中了我,让我十分难忘,您说,我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过完余生。我常常对自己重复这句话。
布罗茨基:我并不认为我将在这里再活一个三十二年,就像在祖国一样。总的说来,这是很难设想的。(不过,如果我在这里活得更久,我的这个说法即便就纯粹的统计学意义而言也很难经受住批评了,是这样的吗?)要知道,无论是我们的信念还是我们的原则,当时在某种程度上都已经形成了。我们这些年纪上的人,自主或不自主地就已经是定型的生物了。基础、起跑——都发生在祖国。我们在俄国的存在是原因。今天所获得的是结果。
沃尔科夫:您难道没有感觉到,在您来到纽约之后,恰恰相反,这次移居也提供出了一个新起点的可能性?
布罗茨基:的确没有过。对于我来说,总的说来,并没有过这样一种起点的感觉。
沃尔科夫:那继续下去的感觉呢?
布罗茨基:这种感觉倒是有,从某个时候开始。大约是从三十岁时开始的,我认为。
沃尔科夫:我们谈到了俄国对您的诗有过的不同反响,顺便说一句,在这里,在侨民界,也存在着这样的不同反响。关于其他一些人,那些由于各种不同原因离开俄国的人,人们的评论和议论大致也是这样的。但与此同时,又有什么东西将他们连接在了一起。这就是斯特拉文斯基、纳博科夫和巴兰钦。顺便说一句,他们三个人从前都是彼得堡人。他们都是我所言的彼得堡现代主义“外国分支”的代表。在这里,在西方,他们从某种民族性的东西转向了更有包容性的东西。他们成了世界主义者。(这个词在这里,在西方,没有任何贬义。它的含义归根结底,就是“世界公民”的意思。)就是因为这种世界主义,有人出面反对他们,所用的说法与对您的攻击相当相似。
布罗茨基:您知道吗,这个问题我还没有考虑过。我说的是实话。我也从来不在这个天地、这个层面打量我所做的工作。我所研究的甚至不是自己的生活,而是自己内心的历史。要看一看我得到了什么,没有得到什么,在我出错的时候,原因是不是在我自己身上。一句话,是一些非常内在的事情。其余的一切我都不是很感兴趣。
沃尔科夫:这个问题之所以让我感兴趣,是因为我越来越坚信,在某个时刻曾有意识地想摆脱俄国文化的斯特拉文斯基、纳博科夫和巴兰钦,最终还是未能脱离俄国文化。结果表明,要想脱离自己的文化,这是不可能的。他们拒绝了某些东西,但他们又获得了一些新的素质。其结果,他们借此又令人难以置信地拓展了俄国文化的疆界。如今在祖国,许多人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个事实。在那里,如今正展开一个过程,即对彼得堡文化外国分支的各项成就进行吸收和同化,这个过程是缓慢的,却是注定的。与此同时,也能看到一些注定会有的企图,想让这一进程停下来。
布罗茨基:这一切都很有意思,不过我个人倒是什么都没拓展。我在写着自己的小诗,仅此而已。我对此没有任何其他的概念。和您提到的这些杰出先生们不同,我甚至不想离开俄国。我是被强迫的。我当时给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写过信,让他们最好能允许我参加祖国的文学进程,哪怕是做个译者也行。可是他们不允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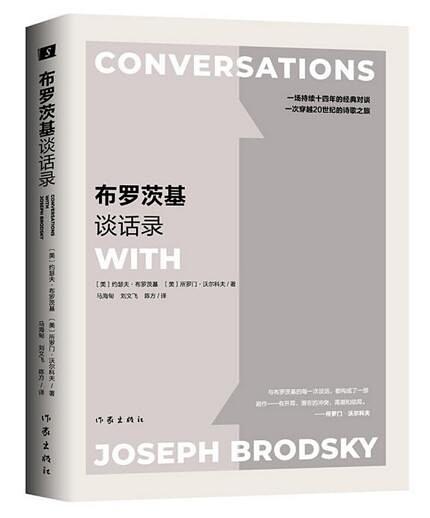
[美] 约瑟夫·布罗茨基 / 所罗门·沃尔科夫 著 马海甸 / 刘文飞 / 陈方 译
作家出版社 2019-04
沃尔科夫:顺便问一句,在最近一期的《纽约人》上,我看到了您的一首诗,它是用英语写成的吗?
布罗茨基:不,这是译文。只不过没有标明译者的名字。顺便说一句,译者就是我自己。
沃尔科夫:我早就知道,您毕竟是会开始用英语写诗的,虽说您相当坚决地强调过,您不想这样做。
布罗茨基:我几乎没有这样做过。我唯一经常用英语写作的东西,就是散文。就是在这一领域,近来也出现了某种停顿。原因就在于,这该死的纽约暑热,热得简直让脑袋转不起来了。
沃尔科夫:非常想看到这些散文——全部的散文——能在苏联出版,被翻译成俄语。一个并不次要的原因就是,这些散文的创作出发点,就是对世界文化的参与。而在那里,在俄国,如今所缺乏的恰恰是这个。
布罗茨基:问题的提法并不完全是这样的:“他们那里缺乏什么。”他们缺乏一切东西。您知道吗,地理学可不是白白存在的。有一些东西是不能被混淆的,是这样的吗?当然,对世界文化的眷恋是存在的。但是要知道,这种眷恋只存在于某种特定的文化中。比如说,在英国文化中就不存在这种眷恋。
沃尔科夫:因为在那里,世界文化一直存在,不需要任何眷恋。
布罗茨基:就某种意义而言是这样的。不过,比如说,英国人反而有一种对东方才有的那种天然浑成的眷恋。他们有一种对东方文化、对所有这些印度因素的向往。总的来说,每一种文化都总是喜欢追求它所缺乏的东西。追求更充分地把握生活,是这样的吗?正因为如此,它才成了文化,这么说它,就像是一只想抓自己尾巴的猫。不过,如果谈到私人层面,英国人,比如说,又是非常唯理论的。至少从外表上看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他们会经常忽视这些细微差别,所有这些所谓的“细枝末节”,所有这些边边角角……我们假设,你切开一个苹果,削去了果皮。现在,你知道苹果内部是什么样的了,但是这样一来,你却失去了苹果那两面都圆鼓鼓的外形。俄国文化所感兴趣的恰恰就是苹果本身,它会为苹果的颜色、表皮的光滑等等而开心。至于苹果的内部,它始终一无所知。草率地说,这就是不同类型的世界观:唯理论的和综合性的。
沃尔科夫:但是,当一个与一种文化类型相关的人又掌握了另一种文化的工作机制,这便能开辟出一些新的地平线来。在这一方面,斯特拉文斯基就是一个杰出的例子。他很早就冲出了祖国的界限。冲出去之后,他又给了整个世界音乐以令人震撼的推动。但是与此同时,现在也看出来了,斯特拉文斯基也对20世纪的俄国音乐产生了最巨大的影响。也就是说,斯特拉文斯基步出俄国文化,是为了永远留在俄国文化中。
布罗茨基:很可能。问题在于,这就是同时属于两种文化,或者更简洁地说,这是一种双语现象,你是注定要落入这一状态的,或者是相反,这究竟是一种祝福,还是一种惩罚,啊?这是一种非常出色的心理状态,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因为,你就像是坐在一座山的峰顶上,看着两侧的山坡。我不知道,在我身上是否也有这样的情形,但是至少,在我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的视点是不错的。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布罗茨基谈话录》一书,较原文有删节,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