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多年前的路,已不再是碎石道路和沙尘漫天,人的衰老不过一二十年的事,王朝也一样,而一个旅行地只需要三四年光景便会变得面目全非,旅行者的噩梦便是旧地重游,被碾碎的和被重构的,似乎都在催促我,勿要恋旧。

古丝绸之路,它一路沿着巍峨的山脉、荒凉的戈壁与一座座绿洲串起的丰饶城市,犹如一幅缓缓展开的壁画图卷。这里完全是一片开阔之地,无论是畜牧还是商业,文明还是宗教,历史上它不仅运输“丝绸”,还能找到一切你所想要的。这里的人崇尚智慧,在海洋帝国和现代城市崛起之前,你从来不会用“蛮荒”来形容它。
去年秋天我为了撰写自驾指南第六次前往新疆,一路西行至喀什,再向东南折回和田,去再次碰触那些色彩厚重的历史和史诗,巴扎里的瓜果、木勺与驴车,以及我年少时的芳馨记忆。沿着多年前的路,已不再是碎石道路和沙尘漫天,人的衰老不过一二十年的事,王朝也一样,而一个旅行地只需要三四年光景便会变得面目全非,旅行者的噩梦便是旧地重游,被碾碎的和被重构的,似乎都在催促我,勿要恋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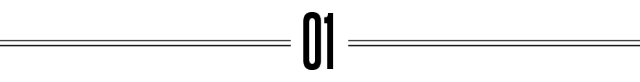
乌鲁木齐至库尔勒

库车巴扎里的小男孩
两天两夜的火车,从成都至乌鲁木齐,我乘坐的是成兰线上最后一趟慢车,从今往后,这条线上大部分列车将缩短十几个小时。和硬卧车厢的一位女孩聊到深夜,过去西去的长途列车上打发时间也时常这样。她在张掖下车的时候,我还在睡梦中,继续往乌鲁木齐,感觉很奇妙。列车跨过戈壁滩,手机的信号,时断时续。我的47个小时,日历从9-29跨度到10-01。

我和维吾尔族朋友迪丽尼卡约在一家领馆巷的烤肉店见面,几年不见,她现在已经是一名检察官了。因为环保的原因,乌鲁木齐很难再找到传统的烤肉店,她问了半天,只有领馆巷里的几家老字号维吾尔族餐馆,还在用电烤箱烤羊肉的方式维系着传统。“领馆”指的是前苏联驻新疆总领事馆驻地,旧址已被拆除。旁边就是洋行清真寺,19世纪中晚期,清政府与沙俄签约,将此段划为租界,俄商在此开设商行,民间称“洋行”。
吃完我们去了趟附近的海尔巴格餐饮美都,这里有很多民族特色的糕点,进门时要过安检,迪丽尼卡对保安说了声:“他是游客。”保安对我笑了笑,让我从侧面进去了。而六年前在乌鲁木齐,她一般对别人说我是美国来的摄影师。
晚上我想去最有民俗风情的地方,迪丽尼卡说那我们去大湾吧,她显然误会我的意思了,我的民俗概念是滞后的、游客化的,而任何一种民俗都在变化,新疆更是在加速变化,除了供游客观赏消遣的新疆歌舞外,至少在乌鲁木齐,已经找不到我以为的那种民俗风情了。大湾那里有许多西式的咖啡厅,男服务生穿着紧身的西装夹克,连咖啡杯都是国外制造的,我们点了两杯咖啡,聊最近几年的近况。迪丽尼卡指了指服务生,说新疆的男人嘛,以为自己很国际化,其实现在的国际化早就变了。
回去的出租车里的电台放着周杰伦的《东风破》,等一个红灯的时间,迪丽尼卡换到了后座,和我并排坐着。她感叹说:“周杰伦都结婚了。”是啊,好多年过去,许多人已不再联系,那些徐州饭店、陕西补胎、浙江宾馆里的人是不是还在浪迹,我表示疑问,只有戈壁滩上的石头永远住着我的回忆,可我却不知道自己要住在哪里。
谁都无法阻止遗忘,就像吐鲁番的古城和佛塔,多少工匠留下的恢弘一笔,都会被无情的大漠黄沙和乌苏啤酒勾销。
吐鲁番城郊还能看到一些传统的民居,高门梁的彩色院落,杨树下布满灰尘的皮沙发,供销社式的粮油铺,和记忆中留存的片段一样。洒水和喝茶是早上的仪式,天刚破晓,最显眼的建筑是成片的葡萄房。
吐鲁番号称世界最大的露天博物馆,你会发现这里旅游开发得有些过度。百公里长的火焰山从吐鲁番延伸至鄯善,其中一段公路边的西天取经雕塑被围起来成为火焰山景区,十四年前,年少的我也曾搭车到此,在雕塑前留影一张。柏孜克里克千佛洞隐身于火焰山中的一个峡谷,规模不及库车的克孜尔千佛洞,壁画也残破不堪,不过风景犹然。
交河故城是1700多年历史的生土城市遗址,传说玄奘当年对高昌王的情谊感念至深—“决交河之水比泽非多,举葱岭之山方恩岂重”,但归来时,高昌已是故国。落日之前走进这座空旷的交河故城,眼前有几分与约旦佩特拉古城相称的风光。作为车师人的旧都,交河故城存续过数百年时间,而倾塌不过数载。几分相似,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奥斯曼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的一章中写道:“历史好比人生,抱憾的心情无法使业已失去的一瞬重返,绝无仅有的一小时,所贻误的,千载难以赎回。”
从吐鲁番出来后是一片非常壮观的像沙漠绿洲一样的禁牧区—骆驼刺草场,继续往前路右有一个大墩烽火台,然后便是风大时火车都能刮得翻的风城托克逊。车过“干沟”,道路两旁山石嶙峋,地貌壮观,黑色岩石与流沙交替,干涸的河床有种悲壮之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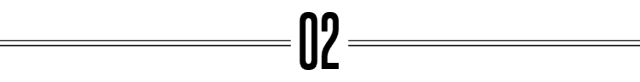
从库尔勒至库车

沙漠公路里的古胡杨林
车行驶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库东公路,一路都是盐碱地、沙地,150公里没有人迹,只有一头一尾的动物防疫检查卡。风卷着流沙从路基上横过,忽见一只戴胜鸟顽固的停在道中央,一如多年前搭车的我。
来到沙漠公路边的小镇,遇到一位出租车司机是四川自贡人,18岁随石油钻井队到了塔克拉玛干沙漠,没想到一待三十年就过了。他脸上全是血丝,双颊被风沙雕刻得如戈壁滩上的玉。由于近年来国际油价下跌,他被迫离职,一直在沙漠里跑出租车。
“打算十一过后,就一路开车边玩边回四川,再也不回来了,车打算卖了,房子也不要了。”他说。
一路上听到很多命运浮沉的故事,有的人发了财,有的人还在亡命天涯,不变的是风沙,变的是宿命。只有青春小鸟才有一张不老的脸,等着落叶归根。沙漠公路的深处有不少胡杨林,每棵树造型无一相同,秋天的时候连成一片金黄,沙漠公路迎来了短暂的旅游旺季。
沙漠公路离库车不远,过去到库车才算是真正到了南疆,可如今的库车也是一派新式的包豪斯式的建筑。一条库车河分割了库车的新老城,过了团结新桥便是另外一派世界,我的河这边的亲戚从未去过河那边的库车王府。以前每到周日,团结新桥会变身一个流动、混乱的巴扎,让你梦回古丝绸之路上驼队马帮的年代,现在的星期天巴扎已搬到了正规的集贸市场。
“过来了就回不去了。那时候苦啊,风沙大,租的房子没有顶棚,第二天人都是个土蛋蛋。”库车的亲戚说道。现在他们仍然没有赶上好时候,未从房价增长中收益,但已经熬过来了,如同所有的入疆者一样,他们很少抱怨。

前往独库公路的时候,干燥的库车难得下起了大雨,听说独库公路大雪封山,我们绕过那个封闭的路段,直到看到塌方的隧道才死心,不过也独享了天山上醉人的湖泊、牧场与峡谷。下山时我来开车,“Z”字形的盘山公路有惊无险,2014的深秋走过独库公路的北段,那些破碎的山河沟堑依旧。已过去好几年了,感觉世界再大,不过是率土之滨,旅途再精彩,又怎比得上际遇。
第二天为了赶拜城魔鬼城的日落,错过了加油时间——这里的加油站日落后就关门,为弄到油我们在警察局门口站了很久,加油站才破例为我们开了门,加完油一刻不停地赶回库车。第三天我开着一辆微型货车,帮叔叔去塔克拉玛干边缘的塔里木乡送酒,来回两百多公里,路过一大片沙漠。车是他一万多块钱买的二手,走到限速带时就必须猛踩刹车,不然剧烈的震动会让空气中灰尘的颗粒都清晰可见,我就像马里奥采蘑菇一样,通过好像数不清的限速带。
此后我每天都要走几百公里的路,戈壁或是沙漠,有许多难忘的故事,更多已变作旅途的日常。阿克苏温宿县有一处苏力塔尼木买合木提布祖尔尕古墓群,在县城北面凸起的山坡上,风化的古墓群连绵几公里,既有墓门高大气派的拱北,也有许多高高低低的平民墓冢,最气派的就是温宿郡王之墓,四方形的墙体连着四个圆形的角柱,周身残留着彩色的琉璃瓦,温宿古为姑墨国,但更多的墓塚已经被世人所遗忘,无从考证。
这就像是踏上了一趟遗忘之旅。越往西,离口里就越远,有种莫名的寂寥感,寄了一堆底片去喀什海关,准备去中国最西边的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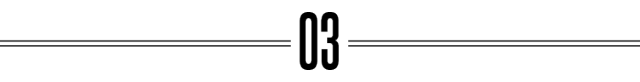
伊尔克什坦

独库公路沿路风景
天山、昆仑山交汇,风吹过陡直坚实的小径,克孜勒苏河像一道回廊,阿富汗胡杨在峡谷里疯狂的生长,像染上了病菌。去了趟中国最西边的村庄,喀布尔的朋友和我也只隔着600多公里。看被地震毁掉的县城,爬上丝路的山隘,穿过孔道,听那些远古而悠长的故事。在吉尔吉斯斯坦边界的一个小商店里遇到一位来自比什凯克的姑娘,她站在一个昏暗的空间里拉着小提琴,琴声让我入了迷。
吾合沙鲁乡的胡杨林是千年阿富汗胡杨林,离通往欧洲的伊尔克什坦口岸不远,附近还有一座藏满化石的贝壳山。胡杨林深处有一个写着“HOTEL”的废弃宾馆,顺石阶登顶是一座古丝绸之路驿站,复原的遗址用砖砌成,看上去好像龙门客栈,过去这一带常有土匪出没,所以驿站建在冲要之地,屹立山顶,俯望峡谷,天晴的时候狭长的河谷中胡杨林和沙棘树林极美。
很多人会专程来中国最西的口岸看一块石头—界碑,如果不是被远方的美景与风俗蛊惑,我觉得我一辈子都不想和口岸打交道。在旅行者里有股风气。“去过的浓烈情结里蕴含着锦标赛式的价值歧视,无论是图片发布还是地理标注,……旅行行为越发成为优越感的炫耀资本。”脾气被旅途磨平,路还是要走的,随遇而安—“遇到厨师就问料理的事,遇到司机问车子的事,遇到和尚就谈另一个世界的事,什么都好。”

拜城魔鬼城
路上有很多欧洲开来的房车与摩托车,而集装箱货车都是来自吉尔吉斯斯坦,车速极快,据说吉尔吉斯斯坦的司机们克服高反的方式是喝俄罗斯的伏特加,我们就在这些长龙中穿梭,为了限制他们超速,前方是警车开道。司机是柯尔克孜族,柯尔克孜就是吉尔吉斯的中文异译,他也老想超车,还试图超过警车,我劝他前面是警车不能再超了。
他一路上都在跟我讲解,“吉根”是什么意思,“乌鲁克恰提”又是什么,哪里有当地人也不知道的古驿站。他跟我聊起在乌恰地震中逃生的经历,被摧毁的县城位于黑孜苇乡,地震残留下的房屋还在,他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哪里是中学,哪里是公安局。遗址的中央是一个巨大的时钟裂痕,时间永远定格在1985年8月23日20时41分。距离地震遗址不远的康苏镇有44栋俄式的“红房子”,建于上世纪50年代,是中苏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留下的。
我们仿佛还存活在一个二手的时间里,只可惜一切已经改变,我再没有见过记忆中小酒馆里那些弹冬不拉的牧人们和穿红色艾德莱斯绸的阿尔孜古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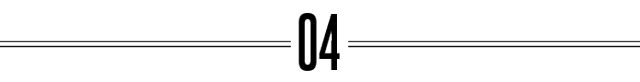
喀什至和田

苏力塔尼木买合木提布祖尔尕古墓群
喀什色满宾馆里一座铁皮尖拱盖顶的建筑是以前的沙俄领事馆,后来又是苏联领事馆,撤销后被改为宾馆。色满宾馆的其他部分像迷宫一样,透露着80年代的味道,指示牌上还有中英日文,对过去走丝路的外国旅行者来说,这里是昔日的天堂。但现在的旅行者都会居住在喀什老城景区,喀什正在变成一座更加旅游的城市,不会再充斥着各色的探险家了。
从喀什到了莎车,2011年我搭车至莎车而不入,现在弥补了这一遗憾,只是再也没有布满尘土的叶河大桥了,那时灰尘能没过脚踝,月亮就像伸手可及。花数亿修建起来的新城看上去空无一人,而到了老城,莎车才活了过来。
在莎车阿勒屯清真寺北侧的陵园,守墓的乞讨者成群结队的出现,守护陵园,靠着源源不断的为故人祈祷的朝拜者的施舍度日。陵园被宁静肃穆的气氛包围,泥土小径和葱郁的树木之间,大大小小的陵墓错综分布,墓前常有人念念有词。陵园内有一座五百余年历史的其勒坦麻扎,昏暗的墓室中布满了华丽又神秘的彩色布条,门口有一位专门的守墓人,所有的朝拜者都会来此祈祷。
在维吾尔的文化中,探望墓地是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朝圣者们在这里述说身体、心理与精神不适,他们用一些小物品做装饰,标志着他们来过、祷告过,体现了集体记忆与和平信念以及对致命的自然力量——沙暴、炙热与强风的忍耐。

其勒坦麻扎
在叶城车站我碰到两位从阿里搭车过来的旅行者,脸晒得像玛曲草原上的牧民,听说我在南疆旅行了一个月,不屑一顾的说道:“我只对和田、若羌感兴趣,莎车?最讨厌什么古城了,崭新的规划更好,你看叶城不很好吗,一团和气,破旧不过是旅行者的一厢情愿罢了。”老城的建筑已岌岌可危,无论从情感还是理性角度来说,有些遗憾,留下的影像,下次来,就再也看不到了。
重回喀什,喀什的正午最适合午睡,看着午后的阳光爬过葡萄架,世界上许多事情已失去神秘。当天山上的花再次绽放,五彩斑斓的颜色随意点缀,隐没在雾气中的树正在生长时,我会再回来的,却不知道会是多久以后了。莫问前路,愿你们都有美好的前程。






